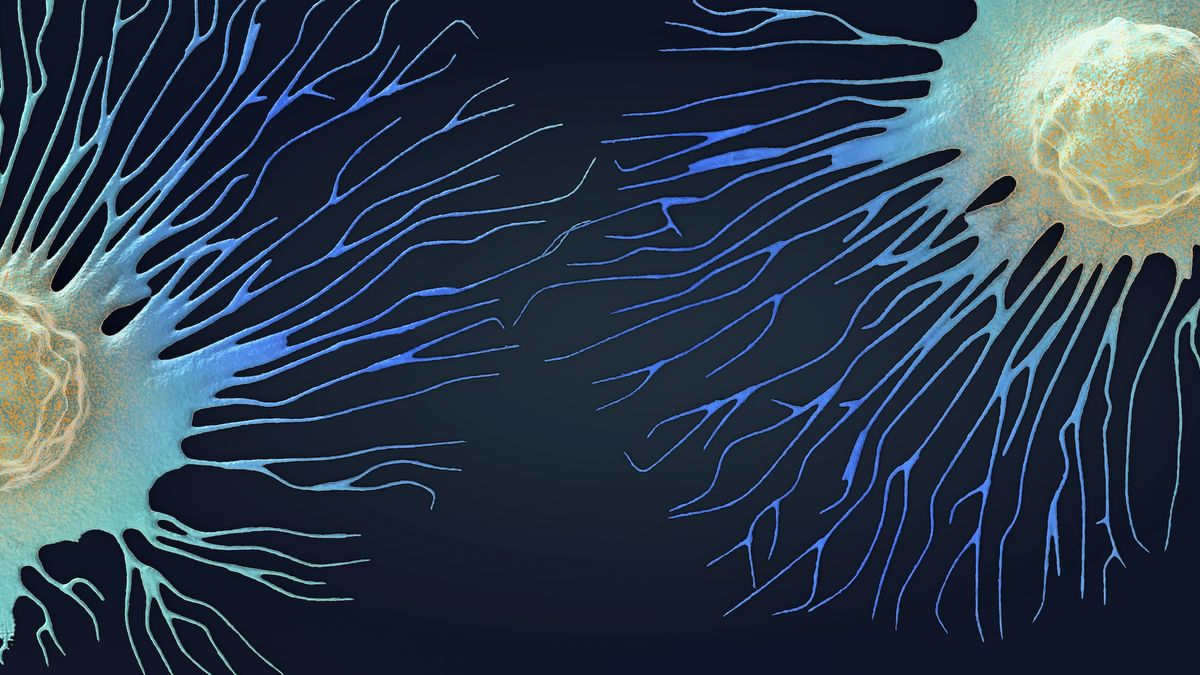IngridaDomarkienė研究古老的DNA,將現代人類的遺傳物質碎片和我們長期滅絕的人類親戚融合在一起,以重述他們的故事。
從分子生物學和醫學遺傳學的背景來看,Domarkienė現在率領立陶宛的第一個古代脫氧核糖核酸實驗室,總部位於醫學科學中心在維爾紐斯大學。該實驗室與國際合作者一起研究波蘭中世紀群眾墳墓中的人們的遺體,以了解當時該地區普遍存在的社會實踐以及立陶宛的鐵器時代個人的遷移。
他們還揭示了1986年在1986年災難的後果的見解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研究人員查看參與清理工作的立陶宛工人的DNA,研究人員確定了有助於防止輻射影響的基因。
現場科學與Domarkienė交談,Domarkienė也是Vilnius的副教授,詢問她的研究,與研究古代DNA相關的獨特挑戰,以及我們對遺傳史的研究如何導致今天的醫學進步。
有關的:DNA研究表明,現代日本人來自3個祖先,其中1個未知。
艾米麗·庫克(Emily Cooke):您覺得很有趣的古代DNA是什麼?
IngridaDomarkienė:令人著迷的是,如何從DNA片段中重新組裝故事,您知道:您只是序列DNA;這是一種技術。
對我而言,來自分子生物學,它是如此有趣,以至於您閱讀了生化片段,有機分子,然後將其與其他樣品進行比較,並且您會看到人們如何移動,來自哪裡,去哪裡,生活方式。您可以獲得“混合信號” - 這意味著(來自不同人群)的人們可以了解誰認識誰以及他們如何繼續前進,您可以重述他們的故事。
EC:研究古代DNA有什麼獨特的挑戰?
ID:最關鍵的挑戰是您必須在這裡擁抱不確定性和失敗。這是為什麼?因為您永遠不確定您是否會獲得進一步工作的DNA質量和數量。
那是因為,當生物體死亡時,DNA開始腐爛,並且沒有像活細胞那樣修復DNA的地方。因此,它開始碎片,並變化成分。更重要的是,它與所有其他環境DNA,當提取時,它看起來為污染。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喜歡五彩紙屑的類比,或者在慶祝活動之後剩下的東西。
EC:您能談談您對切爾諾貝利倖存者的研究嗎?
ID:切爾諾貝利倖存者 - 清理工人或清算人,也稱為。
這是我們與人類和醫學遺傳學系的同事一起的項目,在小組中,我們有分析切爾諾貝利清算人的基因組的想法,我們邀請他們參與研究。當他們開始來的時候,我們聽到了他們的故事,我們明白了 - 您知道,這些人經歷了很多,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沒有癌症的情況下健康地衰老。您可能會期待他們經歷過的最糟糕的結果,但是它們還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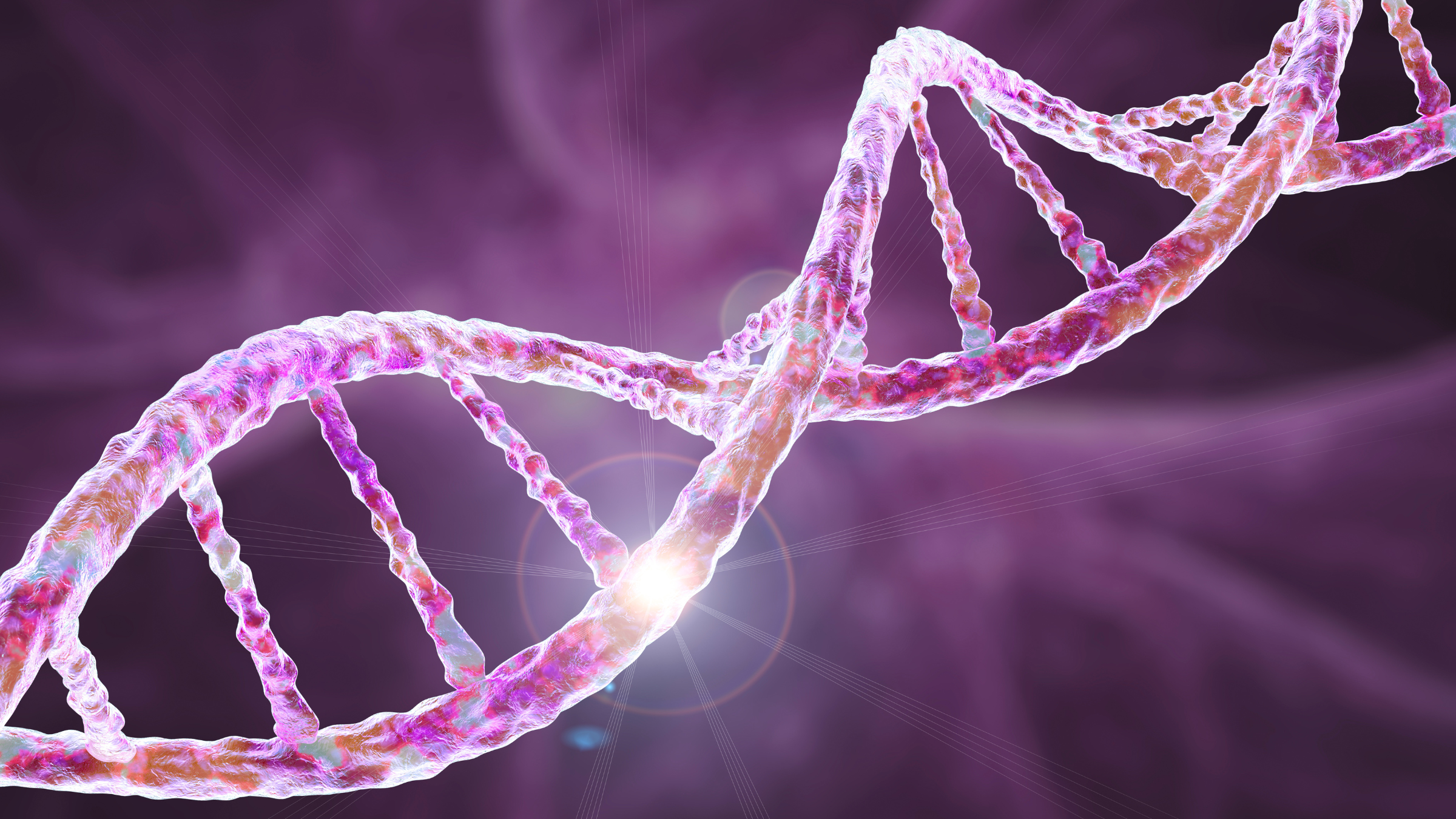
然後我們得到了這一假設:那些倖存者的基因組中可能有一些東西可以保護他們免受發生的一切壞事的侵害,可以說 - 當時的心理壓力,當時是巨大的,當時它們是從當時的地點帶走的,並帶到了切爾諾貝利,沒有說任何話。他們在講述他們如何被醒來的故事,他們只是在火車上坐在那裡的上帝知道哪裡。
當然,那是一個困難的時期,他們不僅要在清算工作中努力工作,而且還試圖將理智置於這種位置。
因此,我們開始分析它們的基因組,並發現了一些保護性變異的潛在信號。然後,我們還撰寫了這篇由我們的學生撰寫的新論文線粒體DNA。因此,這些切爾諾貝利清算器可能在線粒體基因組和核基因組(核中的DNA)中也具有保護性變異,支持線粒體功能。所以也許這就是主意。
EC:研究我們的遺傳史如何幫助我們應對當今的醫療挑戰?
ID:通過古老的DNA研究過去是基礎研究,需要時間才能意識到發現是什麼以及如何在實踐中實施它們。也許最重要的要素可能是您可以信任的強大跨學科團隊,而您實際上不能獨自做任何事情。
我發現SvantePääbo作為基準的示例:您如何在不提及斯文特的名字的情況下談論古代DNA?
他和他的團隊開發了整個古生物學領域,並產生了尼安德特人的參考基因組。他們開始為我們提供解釋人類和尼安德特人序列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以功能方式的含義。例如,SvantePääbo的一位科學家之一,雨果Zeberg博士,與同事一起發現,孕酮受體中的尼安德特人變體與早產有關防止流產,並導致更多的活產。這些知識可以轉化為婦女挽救懷孕的真正幫助。

或者,另一個愛情故事:宏基因組學[對環境中所有生物的遺傳物質的研究],這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領域。但是,正如我們剛剛見證的一種大流行者一樣,它可以幫助感染疾病,並且隨著氣候的變化,可能還有更多。因此,在重建病原體的基因組和建造系統發育樹的基因組[物種之間的進化關係圖]時,我們可以理解病原體的發展和傳播方式。
通過這些分析,我們甚至可以開始新的敘述。例如,很久以前,人們認為西班牙人將結核病引入了新世界。但是教授約翰內斯·克勞斯(Johannes Krause)[Max Planck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團隊]表明,細菌在哥倫布之前就在那裡,顯然是被海豹帶來並轉移到人類,這是居住在秘魯的人們的營養食品。
因此,您可以看到,在這個領域,我們可以給更多的科學和醫學。
EC:您認為古代DNA研究的未來會是什麼樣?
ID: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借助快速發展的技術,我們將能夠在序列中更深入,在數據集中更寬,並且我們分析了更多不同的標記。
因為現在,我們通常分析單個核苷酸多態性或SNP [發音為“ SNIPS”,這是DNA的單個構件中的變化],正如我們所說的那樣。但是我的夢想是重建拷貝數變化,這是[重複] DNA的巨大部分,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但是有一些舉措可以這樣做。
我們還可以進行表觀基因組標記的分析[在基因組上變化的DNA改變了基因的活性而不會影響基本序列],這是分析基因組如何調節的非常好的標記,以了解當時的基因組。那些表觀基因組標記也具有很大的價值。
除了對古代遺址的社會文化結構的分析外,我想說的研究肯定會針對理解我們分析的DNA變異的功能含義。
在大結局中,我們將整合Holoboome。這意味著來自環境的所有基因組信息 - 不僅是人類,而且還包括細菌,病毒,植物,動物,所有居住在那裡的人。並不僅與不同學科的數據集成了這些數據,而且還與我們擁有的不同方法集成。因為數據使用不同的方法出現,並且可以整合所有內容。也許那時我們將擁有完整的圖片。
編者註:為了清楚起見,這次採訪已被凝結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