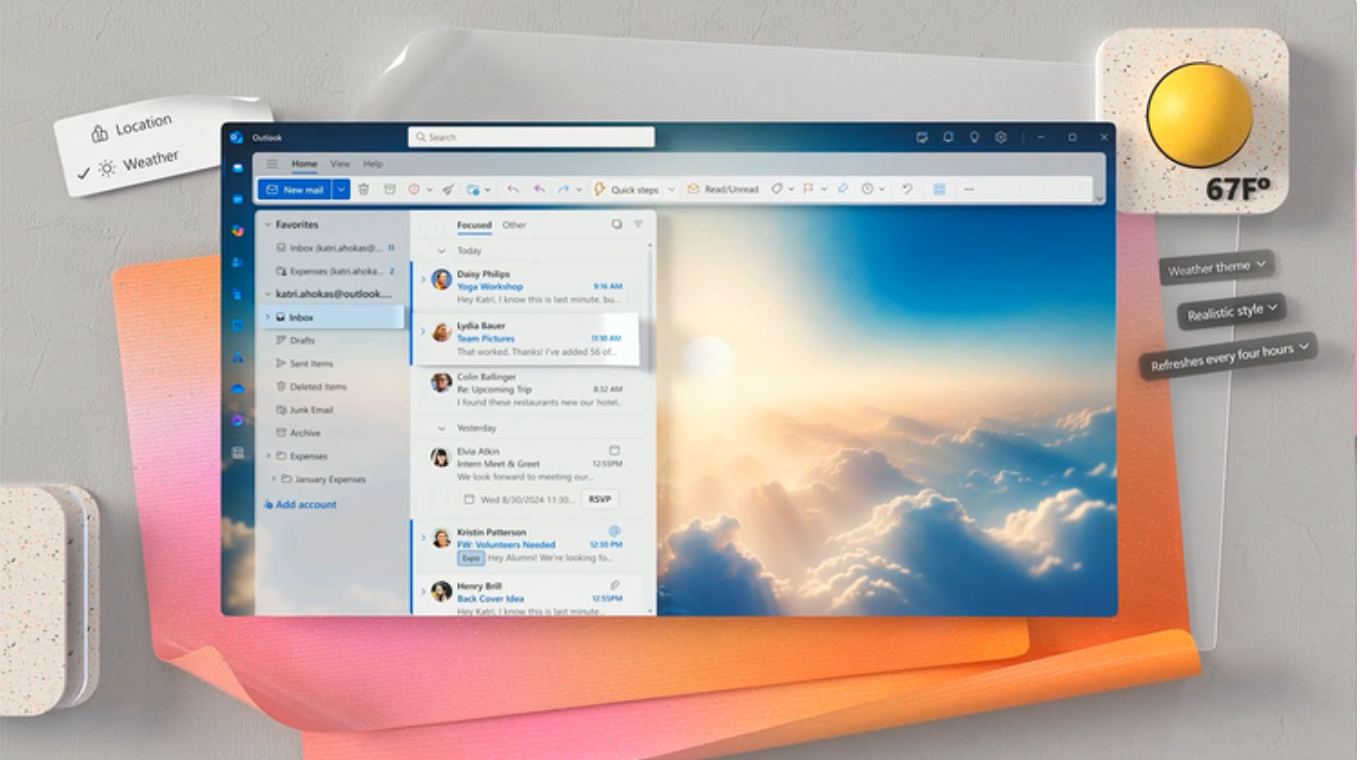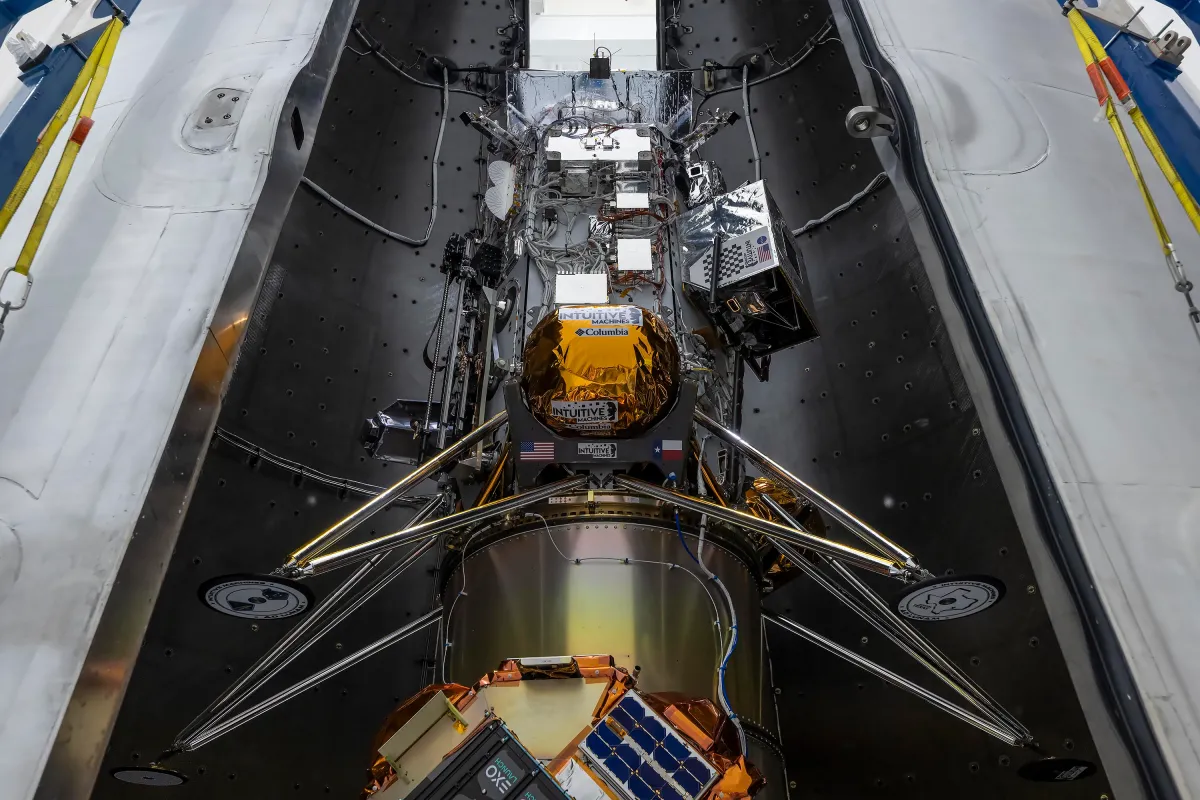小說和大眾媒體中有一種原型或trope式的智力等於隔離 - 當一個人或角色“非常聰明”時,但通常無法與他們的朋友,親戚或任何人的憂慮和個性有關,因此通常會遭受痛苦。
現在,一項新的現實世界研究可能能夠支持這種虛構的原型。來自新加坡和倫敦的進化心理學家發現,即使與親密朋友,聰明的人也很難進行社交互動。
衡量幸福
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的Satoshi Kanazawa,新加坡管理大學的Norman Li最初挖掘出一個問題:是什麼使生活過得充實?
卡納澤(Kanazawa)和李(Li)假設我們的狩獵採集者祖先的生活方式構成了使現代人類快樂的基礎。
他們採用了一個名為“薩凡納幸福理論”的概念來解釋他們的發現,該調查涉及15,000人18至28歲的人。
兩人發現,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地區的人們更有可能報告對生活的滿意度更低。受訪者說的人口密度越大,受訪者說的就越少。
研究人員還發現,受訪者與親密朋友的互動越多,他們自我報告的幸福就越大。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例外:對於聰明的人來說,相關性被逆轉或減少。
請更多一個孤獨的時間
團隊通過人們的智能商來衡量情報。儘管未披露受訪者的確切智商水平,但基線被認為100,而天才水平為140。
卡納澤(Kanazawa)和李(Li)發現,人口密度對智商低的人的生命滿意度的影響是智商高的人的兩倍以上。
實際上,如果與朋友更頻繁地與朋友社交,那麼更聰明的人對生活的滿意程度不太滿意。
換句話說:聰明的人傾向於需要更多的時間。如果他們花太多時間與朋友在一起,他們會對生活不滿意。
研究幸福經濟學的專家布魯金斯學會的卡羅爾·格雷厄姆(Carol Graham)有一個解釋。
“這裡的發現暗示 - 毫不奇怪 - 那些具有更多智慧和使用它的能力的人……花很多時間社交,因為他們專注於其他一些長期目標,”格雷厄姆說。
該人可能更喜歡花更多的時間將癌症視為醫生,寫下他的下一本書,或者努力保護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作為人權律師。頻繁的社交互動似乎損害了他們追求這些目標,對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產生了負面影響。
與我們史前祖先的鏈接
但是,金澤和李的薩凡納幸福理論以不同的方式解釋了這一點。
首先是人類大腦進化以滿足非洲稀樹草原對祖先環境的需求,在非洲大草原上,人口密度與阿拉斯加鄉村相似,每平方公里少於一個人。像現代曼哈頓這樣的環境中這樣的大腦會導致進化摩擦。
儘管如此,我們的史前祖先是狩獵採集者,生活在150個人的小樂隊中。
研究人員說:“在這種情況下,與終身的朋友和盟友經常接觸對於兩性生存和繁殖可能是必要的。”
卡納澤(Kanazawa)和李(Li)發現了一個轉折:聰明的人可能會更好地應對進化變化,因此生活在人口高的地區可能對他們的整體處置和福祉產生較小的影響。
同時,該研究有一個警告:它定義了幸福就自我報告的滿意度而言,不考慮經歷過的幸福感,例如該人上一次笑或該人在過去一周生氣了多少次。
Kanazawa和Li說,這種區別對他們的稀樹草原理論並不重要。
研究人員說:“即使我們的經驗分析……使用了全球生活滿意度的衡量標準,但薩凡納幸福理論並不致力於任何特定的定義,並且與任何合理的幸福,主觀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兼容。”
這項研究是特色在英國心理學雜誌。
照片:艾米·韋斯特|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