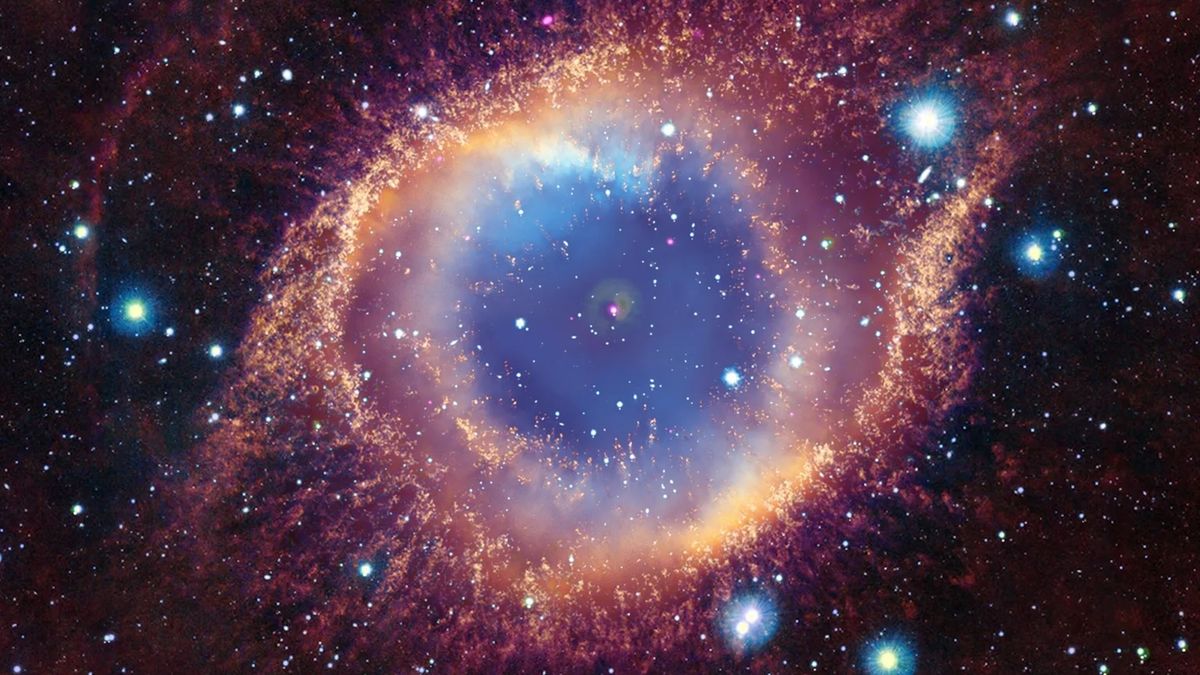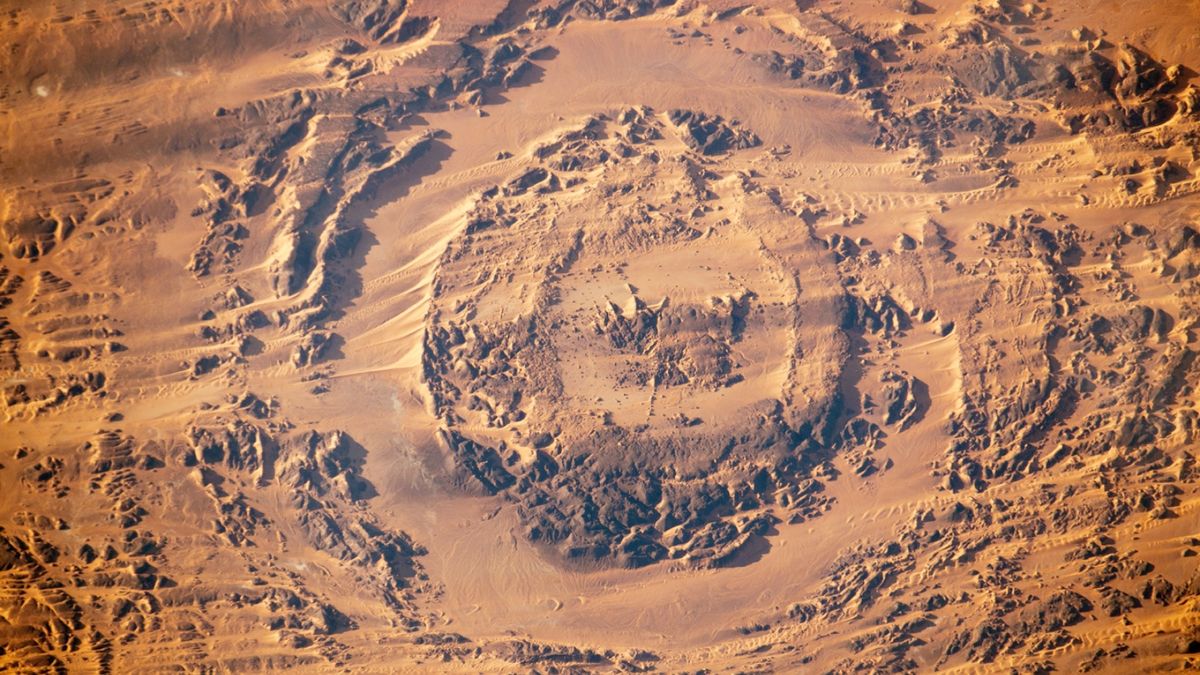社會學家發現,在市政廳會議和博客圈中爆發了關於奧巴馬總統的醫療保健計劃的激烈辯論,與我們的不合邏輯的思維過程有關,而不是現實。
問題:政治過道兩邊的人們經常從堅定的結論中落後,以找到支持事實,而不是讓證據告知他們的觀點。
結果:本週調查發現選民關於他們對計劃的關鍵部分的信念,沿著政黨路線強烈分裂。示例:約有91%的共和黨人認為該提案將增加手術和其他衛生服務的等待時間,而只有37%的民主黨人這樣做。
非理性的思維
一個完全理性的人將在選擇支持或反對計劃之前進行衛生保健的利弊,並客觀地評估衛生保健的利弊。但是我們人類不是那麼理性根據布法羅大學社會學訪問教授史蒂夫·霍夫曼(Steve Hoffman)的說法。
霍夫曼說:“人們對自己的信念深深地依戀。” “我們形成情感依戀,這些情感依戀被我們的個人身份和道德感所包裹,而與事實無關。”
霍夫曼說,為了保持我們的個人和社會身份感,我們傾向於使用落後的推理來證明這種信念。
同樣,伊利諾伊大學烏爾巴納·坎佩恩(Urbana-Champaign)的心理學教授多洛雷斯·阿爾巴拉辛(Dolores Albarracin)的過去研究尤其表明,對信仰不太自信的人比其他人更不願意尋求反對的觀點。所以這些人避免反證據一起。阿爾巴拉辛說,這也適用於醫療保健辯論。
她說:“即使您有自由媒體,言論自由,也不會使人們聽取所有觀點。”
霍夫曼說,幾乎每個人都容易受到持有我們信仰的現象,即使面對相反的鐵桿證據。為什麼?因為很難做。霍夫曼說:“不斷破壞尼采錘子,破壞您的世界觀和信仰體係並評估他人,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挑戰。”
只是您需要的事實
霍夫曼的想法是基於他和同事對近50名參與者所做的一項研究,他們全都是共和黨人,並據報告相信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與薩達姆·侯賽因之間的聯繫。參與者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沒有任何联系,然後要求證明他們的信念是合理的。
(這些調查結果應適用於任何政治傾向。“我們並不是說民主或自由派游擊黨人不做同樣的事情。他們這樣做,”霍夫曼說。
除一個人外,所有人都採用了各種所謂的動機推理策略。霍夫曼(Hoffman)的同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Chapel Hill)的社會學家安德魯·佩林(Andrew Perrin)解釋說:“積極的推理本質上是從您希望達成的結論開始,然後選擇性評估證據以得出結論。”
例如,一些參與者使用了一個向後的推理鏈,其中個人支持決定的決定去戰爭因此,假設有任何支持該決定的證據,包括9/11和侯賽因之間的聯繫。
霍夫曼說:“對於這些選民來說,我們參與戰爭的純粹事實導致事後尋求為這場戰爭的理由。” “人們基本上是為我們在戰爭中構成理由。”
他們的研究發表在最近一期的《社會學探究》雜誌上。
熱醫療保健辯論
研究人員說,擬議中的醫療保健計劃為這種奇怪的推理提供了所有正確的成分。
這個問題既複雜(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改變歷史,雖然辯論經常發生在市政廳環境中的志同道合的同齡人。結果是堅定的支持者和正義的批評者,他們堅持自己的槍支。
佩林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說:“醫療保健辯論將容易受到積極的推理,因為它已經並且已經變得非常情感和象徵性地充滿了信號。”
此外,市政廳的設置使更加僵化的信念。那是因為改變人們對複雜問題的想法會浪費一個人的身份感和社區中的歸屬感。研究人員說,如果您周圍的每個人都是鄰居或朋友,那麼您就不太可能改變自己的意見。
霍夫曼告訴《生命科學》:“在這些一聲的市政廳會議上,您有一個情緒激烈的複雜問題,例如衛生保健,很可能會引起這些令人興奮的情感上的辯論。他們將是熱門辯論。”
雙面討論
為了將事實從雙方帶到桌子上,霍夫曼建議場地一個異質的人可以見面,這些人都需要和反對擬議的人醫療保健系統大修。至少其中一些聚會應包括少數人。他說,在大約六個人的小組中,一兩個成員將傾向於主導討論。
對於任何一方,邏輯參數可能不是關鍵。
佩林說:“從戰略上講,重要的是,奧巴馬政府和衛生保健計劃的擁護者真正關注人們的感受和所看到的象徵意義,而不僅僅是政策的堅果和螺栓。” “人們不會僅憑純粹的事實和邏輯來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