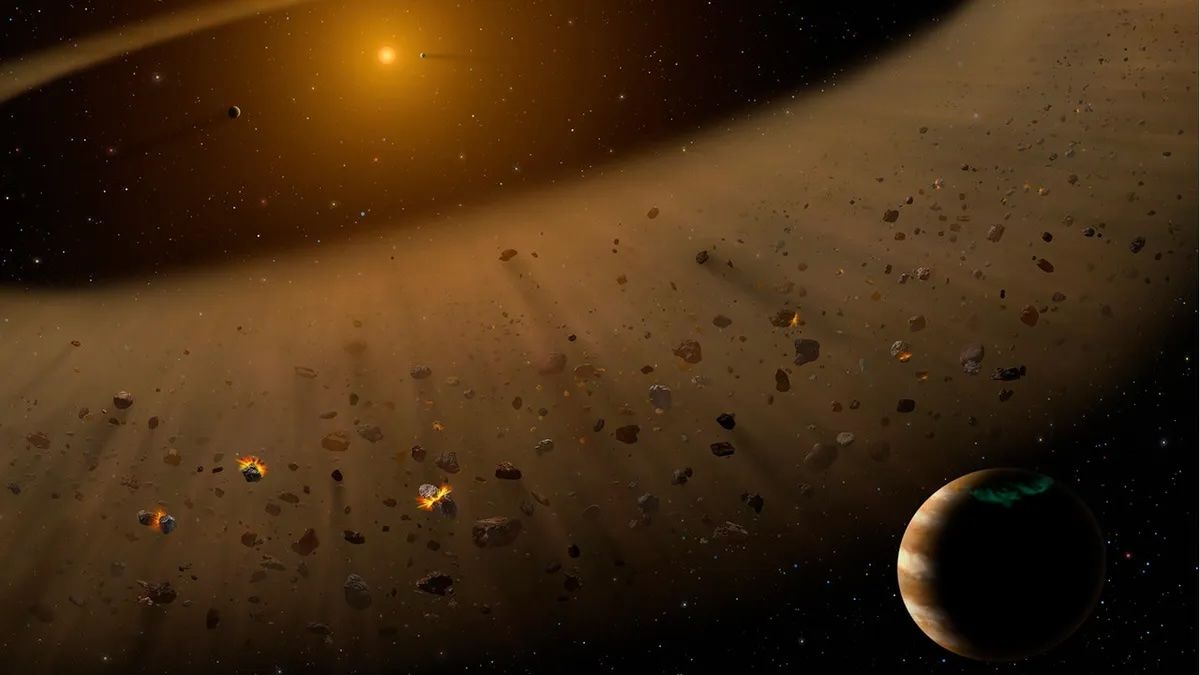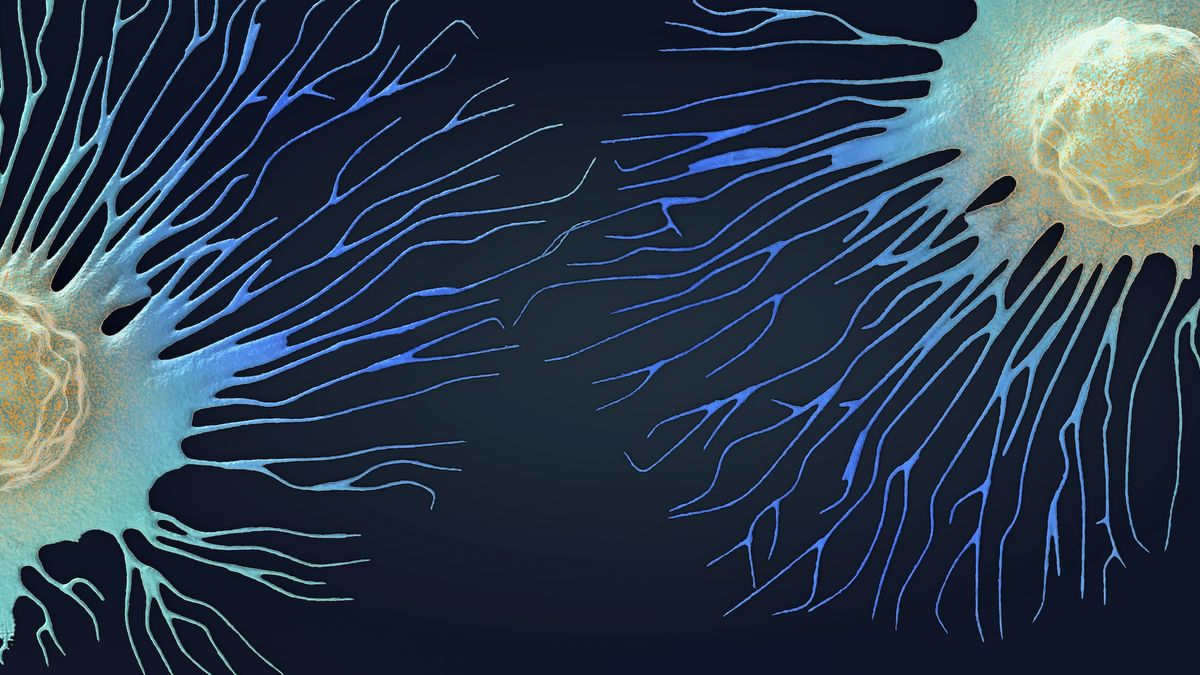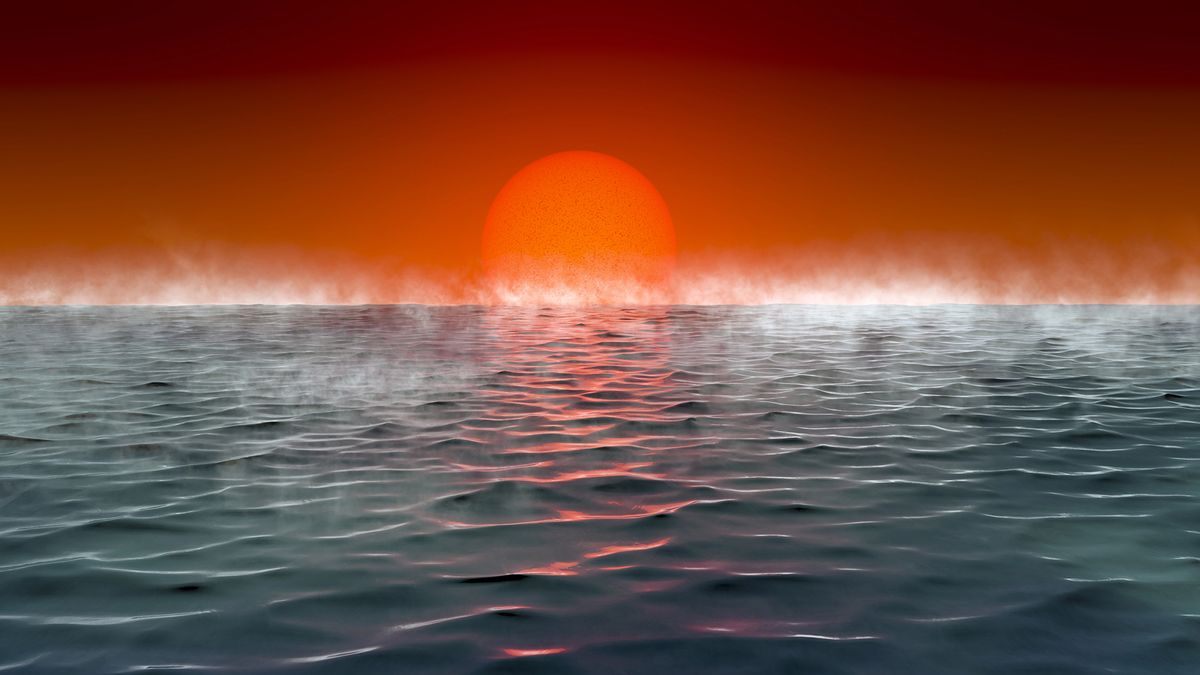我們都知道,無論是注意有毒的蛇,都要注意與自然世界的有毒遭遇。但是,儘管這兩種威脅都涉及毒素,但我們稱漿果為“有毒”,蛇“有毒”。
術語“毒液”和“毒藥”是不可互換的。那麼毒藥和毒液之間有什麼區別?區別更多的是風格而不是實質。
簡而言之,毒液直接由動物注射,而毒藥是被動輸送的,例如被觸摸或攝入。
“如果你咬了它,你生病了,那是有毒的。如果它咬傷或刺痛你,你生病了,那是有毒的。”傑森·斯特里克蘭(Jason Strickland),南阿拉巴馬大學研究毒液的生物學家。
有關的:30種不尋常的有毒動物
在2013年發表在《雜誌》上的研究文章中生物評論,科學家提出了第三類的天然毒素:“毒素”。沒有註射就將毒品被積極噴灑或向受害者扔向受害者。例如,吐痰的眼鏡蛇可以從其牙齒中噴出毒素。
但是毒藥和毒液並不總是以相同的方式工作。例如,毒液不一定會傷害某人,除非它進入血液。佛羅里達大學野生動植物生態與保護系。
無論如何交付,這些有毒化學物質都是捕食者和獵物之間進化的武器競賽中的高效武器。在某些情況下,單一動物可以在犯罪和防禦上使用其毒素。

像黑頸吐眼鏡頭一樣吐痰的眼鏡蛇(Naja Nigricollis)和菲律賓眼鏡蛇(Naja Philippinesnsis),在面對威脅並將毒液注入狩獵的獵物時,會以自衛吐出毒素,使其既是毒素又是毒物的生物。有時,將兩種不同的方法用於相同的目的。火sal(薩拉曼德拉·古多(Salamandra Goodo))用毒素在其皮膚上和毒素從眼睛中噴出的毒素來捍衛自己,使其既有毒又有毒。
從生物學上講,所有這些有毒物質也非常多樣化。僅毒液就獨立發展了超過100次斯特里克蘭說,在像蛇,蝎子,蜘蛛和錐蝸牛一樣多樣的生物中。它們也很常見 - 至少一個估計,約15%地球上所有動物物種都是有毒的。
這些天然毒素中的許多都是由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的化合物組成的。例如,神經毒素(就像那些在曼巴蛇毒液中發現的)攻擊神經系統,而感血毒素(如在銅頭蛇毒中發現的那些)在動物的血液上發動戰爭。
一些莫哈韋響尾蛇(crotalus scutulatus)毒液實際上有神經毒素和血狀毒素既Strickland說,使這些有毒的動物可能“被咬的非常不愉快的物種”。
這些不同的攻擊模式可以反映毒素的使用方式。例如,有毒螞蟻經常將其毒液用作防禦機制,因此會引起立即疼痛以消除入侵者。斯特里克蘭指出,相比之下,蛇毒使蛇能夠餵養受害者,因此蛇可以進食。

同時,一些有毒動物如果攝取會立即死亡,例如屬中的毒龍蛙Phyllobates。這些生物使用batrachotoxin,從而損害體內的電信號,從而有效地阻止了心臟和神經元活性。任何吃它們的捕食者都不會活著吃另一種毒蛙。
然而,一些無毒的生物設法與他們的有毒對手保持同步。負鼠似乎有發展對蛇毒的抵抗力,而蚱hopper小鼠實際上似乎得到了緩解疼痛的效果從樹皮蝎子的刺痛中。
如果毒藥,毒液和毒品之間的區別似乎有些任意,那是因為它們有點是。在某些語言中,“毒液”和“毒藥”都只有一個單詞。例如,在西班牙語中,兩者都被翻譯為“ veneno”,在德語中都被翻譯為“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