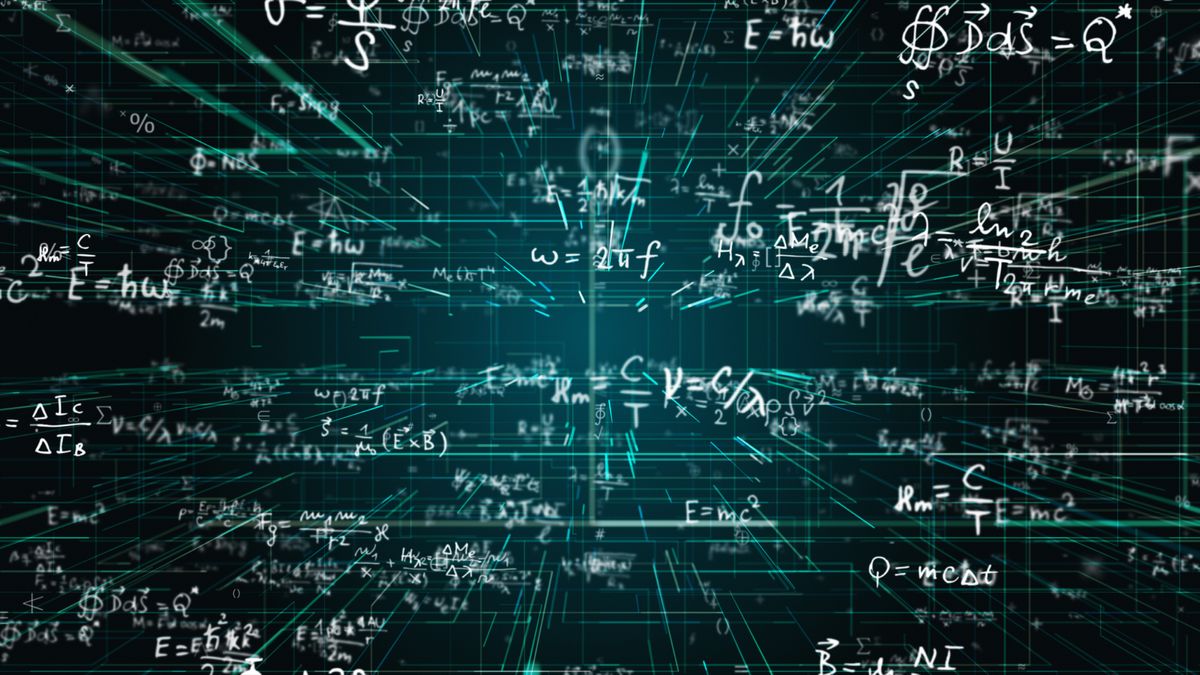美国价值观。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希望收回它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希望恢复它们。纽特·金里奇说他清楚地表达了它们。其他总统候选人、政治家和评论家也对他们有很多话要说。
但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美国价值观是什么?
范德比尔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凡妮莎·比斯利 (Vanessa Beasley) 将“美国价值观”一词比作“美国价值观”。——人们在对称的墨迹中寻找图像。测试促使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事物。 []
“这意味着这群选民想要它意味着什么,”她说。
之后在奥巴马呼吁全国“恢复”美国价值观的文章中,LiveScience 一直在寻找一个共同的定义。大惊喜:我们不仅找到了一个。
正如比斯利所描述的那样,这句话可以提供对我们国家政治言论的洞察,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根据一些将价值观与经济体系联系起来的研究,它还可以为了解我们的集体心理提供一个窗口,并有助于解释我们社会的特征。
四分之三
在他的奥巴马谈到要恢复“一个每个人都有公平机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每个人都遵守同一套规则的经济。危在旦夕的不是民主党价值观或共和党价值观,而是美国价值观。”
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谈到了“我们关于信仰和家庭的价值观”,而竞争对手米特·罗姆尼则提到了“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价值观”。
比斯利表示,所有这些都涉及美国价值观的四种主要解释的各个方面,但今天只使用其中三种。
第一个是经济,即美国梦: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会得到你的劳动成果。
第二个是宗教或道德,可以追溯到我们的清教徒根源,它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变体:我们有崇拜的自由和反对宗教不宽容的权利;或者,美国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国家。
第三个是关于个人主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自己的财富,有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
第四种,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了,就是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所说的公民共和主义,即为了共同利益而做出牺牲的想法——例如,参加战争。比斯利指出,这个版本与个人主义直接冲突。
眨眼
比斯利说,当援引这些国家价值观时,政客们不会具体说明,通常会为听众留下空间,让他们填写自己认为的共同参考内容。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自由”的提及上。这似乎是一个将我们美国人团结起来的理想,除非我们就它的含义进行对话。那么结果可能是我们一个人在谈论经济自由,而另一个人则关心经济自由。,她说。
这种流行语策略越来越成为竞选言论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人们更多地将自己与那些分享自己观点的人结合在一起,而远离那些不认同自己观点的人。
比斯利说:“如果你身处一群与你有着相同信念的人中,你就不必填补空白。”
政治右派比左派更频繁地援引“美国价值观”一词,比斯利将这种不平衡追溯到 1992 年,当时前副总统丹·奎尔 (Dan Quayle) 谈到了他所说的家庭价值观的下降,例如接受。
比斯利说,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试图为左派重新使用这个词。 “我认为奥巴马正试图在经济背景下重新定义美国价值观,以引起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选民的共鸣。”
两个美洲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美国价值观的含义有所不同,诺克斯学院的心理学教授蒂姆·卡塞尔(Tim Kasser)使用了一个框架,该框架根据价值观的外在或内在程度来包含价值观。外在价值观,例如对名誉的渴望或,专注于获得奖励或赞扬,往往更加以自我为导向,而内在价值观,如对社区的渴望,则更加合作。
“事实是,美国有很多外在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卡塞尔说。
例如,在 2011 年《生态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卡塞尔和其他人着手探讨某些研究对象的外在美国性格和其他研究对象的内在民族性格。他们通过构建与双方相关的价值观的简要概况来做到这一点:外在方面包括对财富、经济成功、物质收益、竞争力和“好莱坞理想的美丽、名人和名誉”的关注。内在描述包括慷慨、在需要时团结一致的意愿、自我表达、个人发展和强烈的家庭价值观。 []
经济的反映?
研究表明,如果某一端的价值观被激发,就会导致人们抑制另一端的价值观,并改变他们的行为。例如,他说,讨论金钱或形象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他人的帮助。
他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根源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
研究表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其经济体系强调自由市场的力量,而监管有限,公民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公民更倾向于外在价值观,就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 (根据记录,所有这些国家的人们都认为内在价值比外在价值更重要,但对于拥有像我们这样的经济体系的国家来说,差距正在缩小。)
这种外在的转变使得更加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公民很难关心更加亲社会的内在价值观,因为“同时关心这两套价值观相对困难,”他说。
卡塞尔表示,这具有社会影响。他将一个国家优先考虑更内在的价值,并在许多措施上取得更好的表现:儿童福祉、更慷慨的产假法、减少针对儿童的广告以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他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的一份报告将美国的儿童福祉列为经济发达国家中倒数第二,仅次于英国。
“关键是我们的经济组织……影响公民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最终会影响我们投票给谁以及通过哪些政策。反过来,这些政策和价值观最终会影响我们如何对待彼此,从而影响儿童的福祉,”他在给《生命科学》的电子邮件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