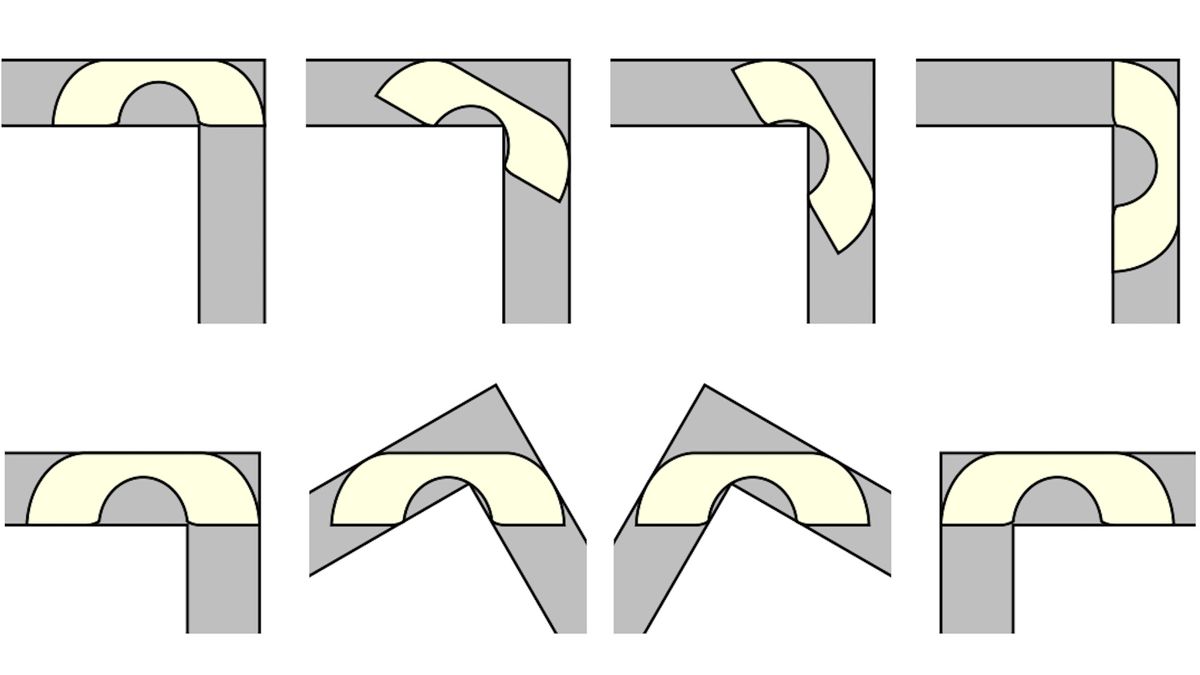從13世紀開始蒙古帝國像野火一樣遍布亞洲,進入中東,成長為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土地帝國。
歷史學家長期以來一直猜測乾旱時期推動蒙古隊征服鄰居,但初步的新發現表明,理論可能完全是向後的。取而代之的是,一貫的雨水和溫暖的溫度可能使蒙古人征服歐亞大陸所需的能源:為他們的馬草。
這一想法是由於發現蒙古氣候歷史至公元657年的樹戒指所帶來的,仍處於調查的初步調查階段。 LiveScience與Dendochmonermonsorks或Tree Tree Researcher Amy Hessl進行了交談,後者與合作者Neil Pederson和Baatarbileg Nachin一起首先發現了保存的樹木,暗示了天氣蒙古時代。
LiveScience:您是如何找到擁有蒙古氣候記錄的樹木的?
赫斯爾:幾年前,我們由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地理學會資助,以研究氣候變化如何影響野火活動在蒙古。因此,我們被這種熔岩流動的驅使,這讓我想起了我在美國西部所知道的其他地方,這些地方的氣候記錄確實很長。樹上生長的樹木乾燥的裸露地點傾向於成長,直到它們真的很老。然後,一旦死亡,木頭就會緩慢腐爛。它使您可以重建很長時間的環境條件。
我們沿著這種熔岩流動,我當時想:“哇,這看起來像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因此,我們回去了,即使我們進行了採樣,我們也沒有任何偉大的東西。我們只是在彼此來回扔掉這些木頭,例如:“哦,我們將其融入咖啡桌藝術中。”我們並沒有真正認真對待它。
LiveScience:您是如何意識到自己發現重要的東西的?
赫斯(Hessl):我把它們交給了我的同事尼爾·佩德森(Neil Pederson)[哥倫比亞大學的拉蒙特·霍蒂(Lamont-Doherty)地球天文台]。他幾個月沒有看著它們,直到他終於沒有其他事情要做,所以他開始與他們約會。我在星期五晚上開始從他那裡得到這些文字,他就像是:“我回到了1200年代。”
最後,我得到了剛剛有三個數字的文字,657。我想:“那是什麼,他要我早上6:57給他打電話?”事實證明,它是最古老,最內在的戒指,公元657年(CE代表共同時代,這一時期與基督教時代相吻合,而某些人則喜歡非宗教的替代方案年,或廣告)
肯定還有其他樹木記錄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地方,但這對蒙古人來說是很特別的,因為它顯然涵蓋了[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的興起時期。 [戰鬥,戰鬥,戰鬥:人類侵略的歷史這是給出的
生命科學:樹環怎麼能告訴您過去的氣候是什麼樣的?
赫斯(Hessl):這些樹木在這種熔岩上生長,土壤發育很少,所以它們確實非常受壓力。什麼時候樹戒指很狹窄,告訴您,在其生長季節,幾乎沒有水。戒指越大,那越濕。
LiveScience:您認為蒙古帝國出現了什麼樣的氣候模式?
赫斯爾:這是非常初步的,但是在那段時間內我們擁有的幾棵樹中,我們可以看到戒指不僅寬,而且在與成吉思汗興起的時代重疊的時間裡,它們始終寬。
我們的推論是,這將是草原上高草地生產力的理想時機,並且可能轉化為更多的牲畜,尤其是蒙古人的馬。
從角度來看,每個蒙古戰士都有10匹馬可以使用。就在那裡,這是需要大量的生物量。除此之外,當蒙古人在旅行和掠奪中擴大範圍時,他們帶來了大量的牲畜來養活自己。他們的整個軍事行動基本上是基於以下事實的。這些氣候條件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能量來促進帝國。 [天氣改變歷史的十大方式這是給出的
LiveScience:蒙古時代後期發生了什麼?
赫斯爾:發生了一個眾所周知的寒冷時期火山噴發後在1258年,我們可以看到蒙古的寒冷,乾燥的條件。同時,在1260年左右,蒙古人將他們的首都從草原上移出並進入了北京,我們認為這也可能是相關的。我們有一位歷史學家,高級學習研究所的尼古拉·迪科莫(Nicola Dicosmo),我們正在與誰合作,他們將重新瀏覽所有中國文件,蒙古記錄和歐洲帳戶,以嘗試查看是否有信息可以證實我們的發現。
生活學:您要回蒙古嗎?
赫斯(Hessl):實際上,我要離開一周了!我們將回到相同的熔岩流並收集其他樣品,因為我們並沒有第一次真正投入其中。我們只在那里呆了幾個小時。
我們還確定了蒙古的其他一些熔岩場,我們認為可能具有類似的生態環境。我們也與其他人合作。一個是研究湖沉積物的華盛頓大學的艾弗里·庫克·史尼曼(Avery Cook Shinneman)。她將從蒙古帝國的所在地Orkhon Valley的湖泊中帶走核心,尋找一點真菌孢子那生活在牲畜糞便中。我們希望我們能在這些湖泊周圍獲得一些牲畜的一般數字和密度。
LiveScience:您對將過去的氣候與這樣的歷史聯繫起來有什麼有趣的?
赫斯(Hessl):考慮以前文明所依賴的能源,以及這些社會的反應方式,以及這些能源的何時,這是令人著迷的能源蒸發,他們是如何適應的?
當今的社會正在應對我們的主要能源的主要威脅,因此,回顧這些早期的文明,看到它們經歷了相同的過渡,這讓我著迷。它只是將我們當前的狀況視為視角。
在Twitter上關注Stephanie Pappas@sipapas或生命科學@livescience。我們也在Facebook和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