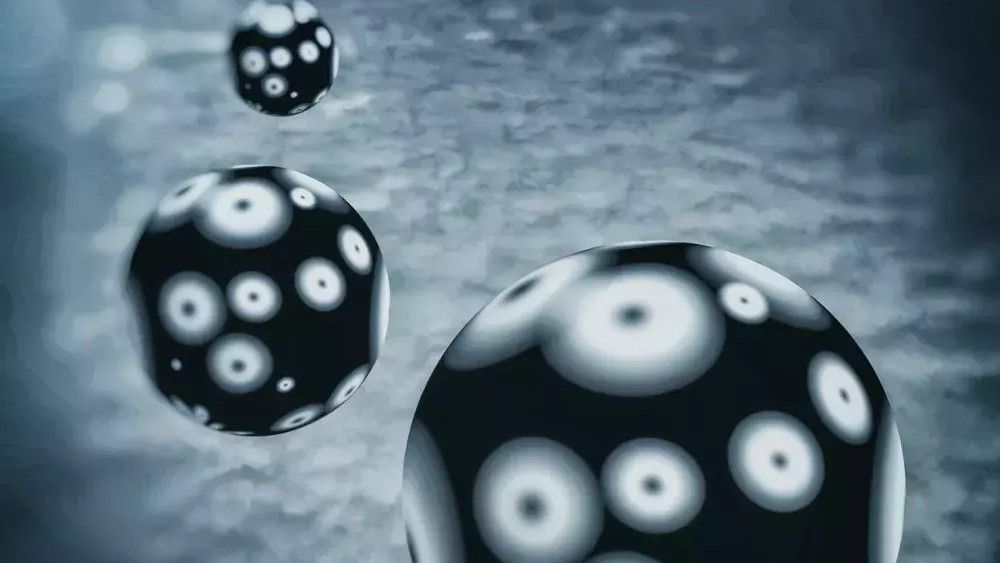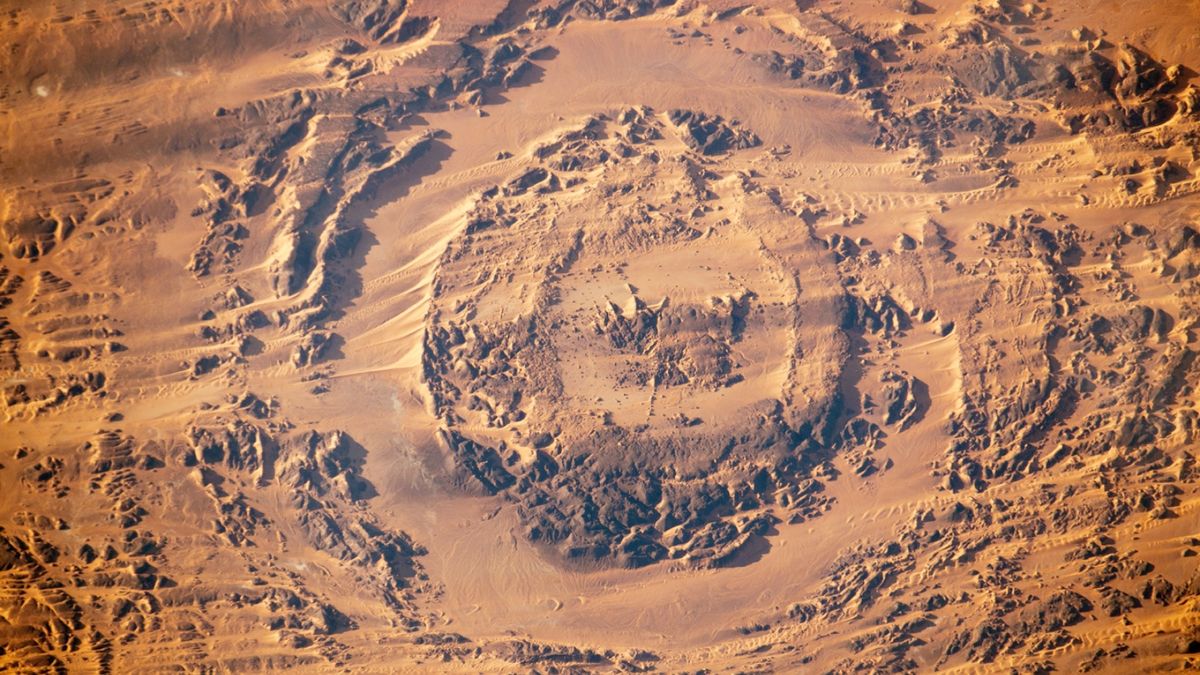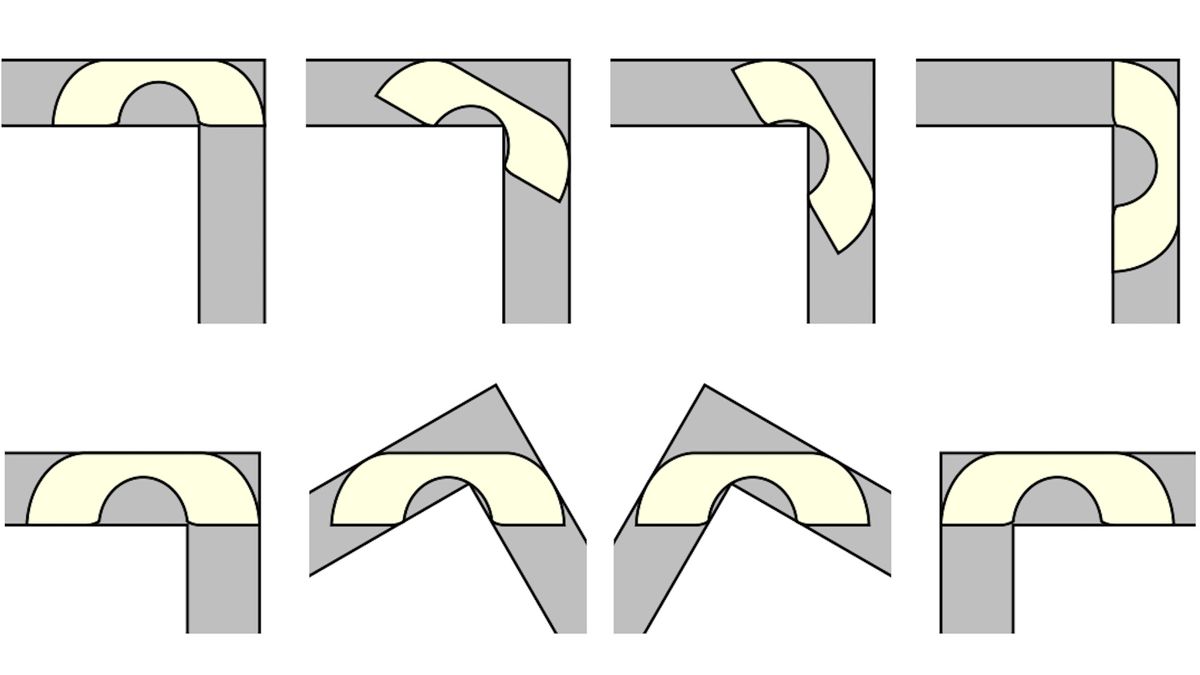評論
說唱歌手坎耶·韋斯特(Kanye West),網球明星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和國會議員喬·威爾遜(Joe Wilson)有什麼共同點,除了對他們最近的公開爆發的宣傳之外,還有什麼共同點?
精神科醫生並不能得出結論,這三個人都將他們的瞬時情感需求放在了他人的感受和願望上,並且他們未能通過遊戲的眾所周知。儘管他們的侵入性行為可能被合理化為“袖口”或“發自內心”,但事實仍然是,這些人中的每個人都在幾秒鐘,幾分鐘或幾個小時內進行了計算:他們計算出他們的憤怒或怨恨比其他人期望的更重要。
當然,我們所有人都會不時“失去”它,自從我們的尼安德特人的前輩首先學會了咆哮以來,不禮貌的爆發可能與我們同在。此外,歷史數據可能不會支持舉止越來越嚴重的印象。約翰·卡森(John F. Kasson)在他的書中粗魯和文明,指出,中世紀的人們的舉止比我們的現代“一切都與我有關!”的表現要繁華得多。人群。卡森援引社會學家諾伯特·埃里亞斯(Norbert Elias)的工作,與最近的時代相比,“……中世紀晚期的人們表達了他們的情感 - 喬伊,憤怒,虔誠,恐懼,甚至是折磨和殺死敵人的愉悅 - 在直接和強度上令人驚訝。”
也許是這樣的 - 但是最近的西部三重黑人,威廉姆斯和威爾遜讓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想知道我們是否正在變成一個自我吸收的布爾人。 (一個波士頓環球報9/15/09的社論宣稱:“大喊大叫是新的主題。”)這篇論文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三十年前,克里斯托弗·拉施(Christopher Lasch)在他的書中提出了同樣的論點文化自戀。但是拉施的主張主要是印象派。但是,現在,許多研究人員和精神衛生專業人員指出,研究表明,確實,過度的自我吸收正在增加。
例如,在他們的書中自戀流行:生活在權利時代,Jean M. Twenge博士和W. Keith Campbell博士提供充分的證據表明他們“在我們的文化中自戀的無情上升”。 Twenge和Campbell確定了一些促成這個問題的社會趨勢,包括他們稱其為“朝向自尊”這始於1960年代後期;從1970年代開始的“以社區為導向的思維”的運動。但是,根本原因進展得更深。作者認為,實際上,已經從限制設定轉向讓孩子得到他或她想要的一切。
Twenge和她的同事擁有經驗數據來支持他們的主張。例如,在2008年8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個性雜誌,作者報告了1979年至2006年之間研究的85個美國大學生樣本。自戀性格清單(NPI)。與1979 - 85年期間的同齡人相比,2006年的大學生的NPI得分增長了30%。那是“壞消息”。如果有一些好消息,那可能就是這樣:Twenge和她的同事Sara Konrath,Joshua D. Foster,W。 KeithCampbell和Brad J. Bushman指出,幾種“積極特徵”與自戀,例如自尊,外向和自信相關。當然,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可能會回答說,這些特徵是“積極的”,直到某種程度上是:當某人的“自信”想法涉及跳上舞台並從屢獲殊榮的歌手那裡抓住麥克風時,可以說,自信就越過了loutishness。
Twenge和Campbell痛苦地擊倒了所有自戀者基本上是自尊心很低的不安全人的神話。他們的研究表明,大多數自戀者似乎都有自尊心的幫助!但是Twenge和Campbell主要關注的是“對文化影響最大的社會自戀者”。這些高流動人可能是我同事定義一個同事之一自戀作為“在高峰性幸福時期,一個人哭了自己的名字!”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名人自戀者並不是我在自己的精神病實踐中接受過的那種人。我的病人傾向於落入Twenge和Campbell小組中,稱為“脆弱的自戀者”。這些不幸的靈魂似乎在金色的地幔中掩蓋了自己,同時感覺到裡面不過是破布。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遭受了痛苦 - 但他們也誘發了他人的痛苦表現出他們的不安全感以一千個挑釁的方式。而且,就像他們的一些名人一樣,這些脆弱的自戀者很容易爆發憤怒,口頭虐待或只是簡單的粗魯 - 通常是當他們感到被拒絕,挫敗或沮喪時。他們想起了哲學家埃里克·霍夫(Eric Hoffer)的觀察之一,即“粗魯是弱者的模仿力量”。
如果我們確實在社會中產生越來越多的自我癡迷的人,我們該怎麼辦?顯然沒有簡單的處方,即明顯的深層文化和家族疾病。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藥房貨架上任何地方都沒有“自戀者的百憂解”。正如Twenge和Campbell所說的那樣,我們養育可能需要改變的孩子的方式很多。我認為,這不僅僅是拒絕破壞或過度沉迷我們的孩子的問題。相反,我們還必須灌輸積極的價值觀,這將有助於接種我們的孩子免受自戀。
在我的書中一切都有兩個手柄:斯托克的生活藝術指南,我認為,古代斯科奇的價值觀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個人幸福。我認為這些相同的價值觀可以幫助我們的孩子成長為強大,負責任和有韌性的公民。什麼是Stoic值?這不僅僅是保持僵硬的上唇,斯多葛主義也不認為您應該抑制所有的感覺。相反,斯托克斯認為,美好的生活是一種以良性信念和行動為特徵的,簡而言之,是基於義務,紀律和節制的生活。斯科奇還相信,以自己的方式奪去生命的重要性 - 他們將其描述為“與自然和諧相處”。
斯托克斯(Stoics)被授予獎勵時並沒有抱怨,也沒有在他們沒有得到的時候就丟了嘶嘶聲。正如塞內卡(公元前106 - 43年)所說的那樣,“所有的兇猛都是弱點。”也許最重要的是,Stoics理解了感激之情的巨大價值 - 不僅是我們收到的禮物,而且還因為我們倖免的悲傷。也許如果有更多的孩子被這些教義灌輸,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名人表現出更多的感激之情,更少的“態度”。
羅納德·派斯(Ronald Pies)醫學博士是紐約州錫拉丘茲(Syracuse)的紐約州立大學紐約州立醫科大學的精神病學教授和生物倫理學和人文學科講師;波士頓塔夫茨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和主編,精神科時代。他是一切都有兩個手柄:斯托克的生活藝術指南。本文由PsychCentra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