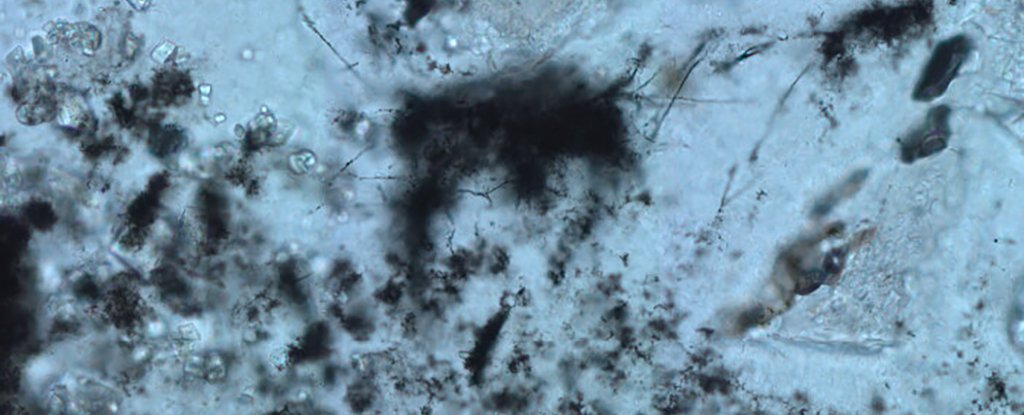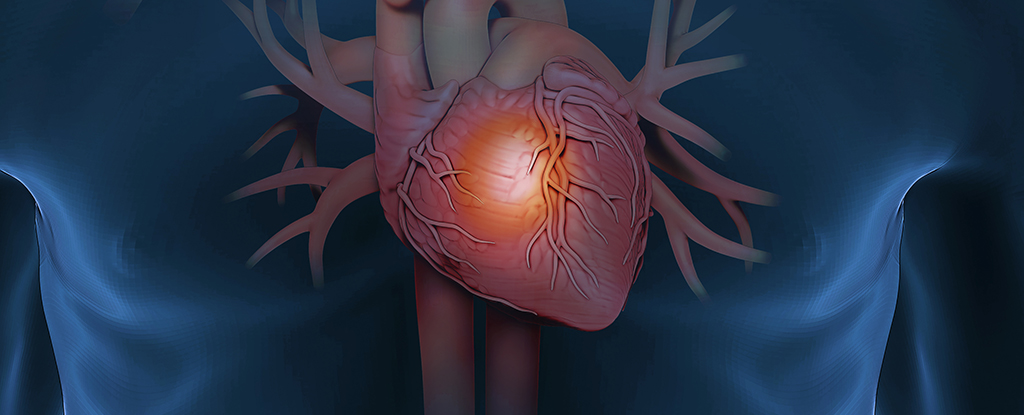的概念精神分裂症快死了。 苦苦挣扎了几十年通过心理学,它现在似乎受到了精神病学的致命伤害,而精神病学正是曾经支撑它的职业。 它的逝去不会被哀悼。
如今,诊断出精神分裂症与预期寿命缩短近二十年。 根据某些标准,只有七分之一的人康复。
尽管治疗方法取得了进步,但令人震惊的是,康复者的比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有些事情是严重错误的。
部分问题在于精神分裂症本身的概念。 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独特疾病的论点一直是“被致命地破坏”。
就像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概念自闭症谱系障碍,精神病(通常以令人痛苦的幻觉、妄想和混乱的思想为特征)也被认为是沿着连续体和程度存在的。
精神分裂症是经历范围或连续体的严重一端。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吉姆·范·奥斯认为,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语言,我们就无法转向这种新的思维方式。
因此,他提出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精神病谱系障碍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精神分裂症被描述为“无望的慢性脑病”。结果,一些给出此诊断的人, 还有一些父母, 已被告知癌症会更好,因为它更容易治愈。
然而,这种对精神分裂症的看法只有排除那些确实有积极结果的人才有可能。 例如,一些康复者被有效地告知“毕竟它一定不是精神分裂症”。
范奥斯认为,当精神分裂症被理解为一种离散的、绝望的、不断恶化的脑部疾病时,“不存在”。
分解故障
相反,精神分裂症可能是多种不同的疾病。 著名精神科医生罗宾·默里爵士描述了如何:
我预计精神分裂症的概念很快就会结束……这种综合症已经开始分解,例如,分解为由拷贝数[遗传]变异、药物滥用、社会逆境等引起的病例。大概这个过程会加速,精神分裂症这个词将像“水肿”一样被限制在历史中。
目前的研究正在探索人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许多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特征的经历:幻觉、妄想、思维和行为混乱、冷漠和情绪平淡。
事实上,过去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误地A路径the或者,更常见的是,将小路误认为是高速公路。
例如,根据他们对寄生虫的研究弓形虫,通过猫传播给人类,研究人员 E. Fuller Torrey 和 Robert Yolken 认为“最重要的病因(精神分裂症的病因)可能是具有传染性的猫”。
它不会。
有证据确实表明接触弓形虫年轻时会增加某人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几率。
然而,这种影响的大小涉及增加不到两倍某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几率。 这充其量只能与其他风险因素相媲美,而且可能要低得多。
例如,童年遭遇逆境,使用大麻,并且有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病毒感染,所有这些都会使某人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例如精神分裂症)的几率增加大约两到三倍。
更细致的分析揭示了更高的数字。
与非大麻使用者相比,每天使用高效、类似臭鼬的大麻与增加五倍某人患精神病的几率。
与没有遭受过创伤的人相比,那些遭受过五种不同类型创伤(包括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人发现他们患精神病的几率增加了超过五十倍。
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其他途径也正在被确定。约1%的病例似乎源于 22 号染色体上一小段 DNA 的缺失,称为 22q11.2 缺失综合征。
也有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的经历可能是由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大脑炎症引起的,例如抗NMDA受体脑炎,虽然这仍有争议。
上述所有因素都可能导致类似的经历,我们在婴儿期将其放入一个称为精神分裂症的桶中。
一个人的经历可能是由具有强大遗传基础的脑部疾病引起的,其驱动因素可能是夸张青春期期间发生的脑细胞之间连接修剪的正常过程。
另一个人的经历可能是由于复杂的创伤后反应造成的。 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也可以结合起来发挥作用。
不管怎样,事实证明,精神分裂症之战中的两个极端阵营——那些将其视为一种基于遗传的神经发育障碍的人,以及那些将其视为对逆境等心理社会因素的反应的人——都有部分谜团。
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单一事物、通过单一途径到达的观念促成了这场冲突。
对治疗的影响
许多医疗状况,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达到,但影响相同的生物途径并对相同的治疗产生反应。
精神分裂症可能是这样的。 事实上,有人认为,上面讨论的精神分裂症的许多不同原因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最终影响:多巴胺水平增加。
如果是这样,那么关于通过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来分解精神分裂症的争论就有点学术性了,因为它不能指导治疗。
然而,有新的证据表明,目前被认为表明精神分裂症的不同经历途径可能需要不同的治疗。
初步证据表明,有童年创伤史的人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抗精神病药物不太可能有帮助。
然而,对此进行更多研究这是必要的,当然,任何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人都不应在没有医疗建议的情况下停止服用。
还有人提出,如果某些精神分裂症病例实际上是自身免疫性脑炎的一种形式,那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可能免疫疗法(如皮质类固醇)和血浆置换(血液清洗)。
然而,目前的情况尚不清楚。 一些新的干预措施,例如基于家庭治疗的开放对话方法,为广大精神分裂症诊断患者带来希望。
可能需要一般干预措施和针对某人个人经历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经历的具体干预措施。 这使得测试并向人们询问所有潜在的相关原因变得至关重要。
这包括儿童虐待,这一现象仍然存在没有被例行询问和识别。
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不同的人有效的可能性进一步解释了精神分裂症之战。 看到的精神科医生、患者或家人抗精神病药物的显着有益作用自然而然地大力提倡这种方法。
精神科医生、患者或家人认为药物不起作用,但替代方法似乎有帮助,赞扬这些。 每个群体都认为对方否认他们所经历过的工作方法。
这种热情的倡导值得赞扬,但人们却被拒绝找到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方法。
接下来是什么?
这并不是说精神分裂症的概念没有用。 许多精神科医生仍然将其视为一种有用的临床综合症,有助于定义具有明确健康需求的人群。
在这里,它被视为定义了一种尚未被理解但具有共同点和特征的生物学。实质性遗传基础跨越许多患者。
一些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人会发现它有帮助。 它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治疗。 它可以增强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它可以为他们遇到的问题命名。 这可能表明他们正在经历疾病,而不是个人失败。 当然,很多觉得这个诊断没有帮助。
当我们进入后精神分裂症时代时,我们需要保留精神分裂症一词的好处并抛弃它的负面影响。
这会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日本最近改名了精神分裂症称为“整合障碍”。 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的“精神病谱系障碍”。
然而,从历史上看,精神病学的疾病分类被认为是一场斗争的结果,其中“最著名、最善于表达的教授获胜”。
未来必须建立在证据和对话的基础上,其中包括遭受这些经历并能很好应对的人们的观点。
![]() 无论精神分裂症的灰烬中出现什么,它都必须提供更好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在真实经历中挣扎的人。
无论精神分裂症的灰烬中出现什么,它都必须提供更好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在真实经历中挣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