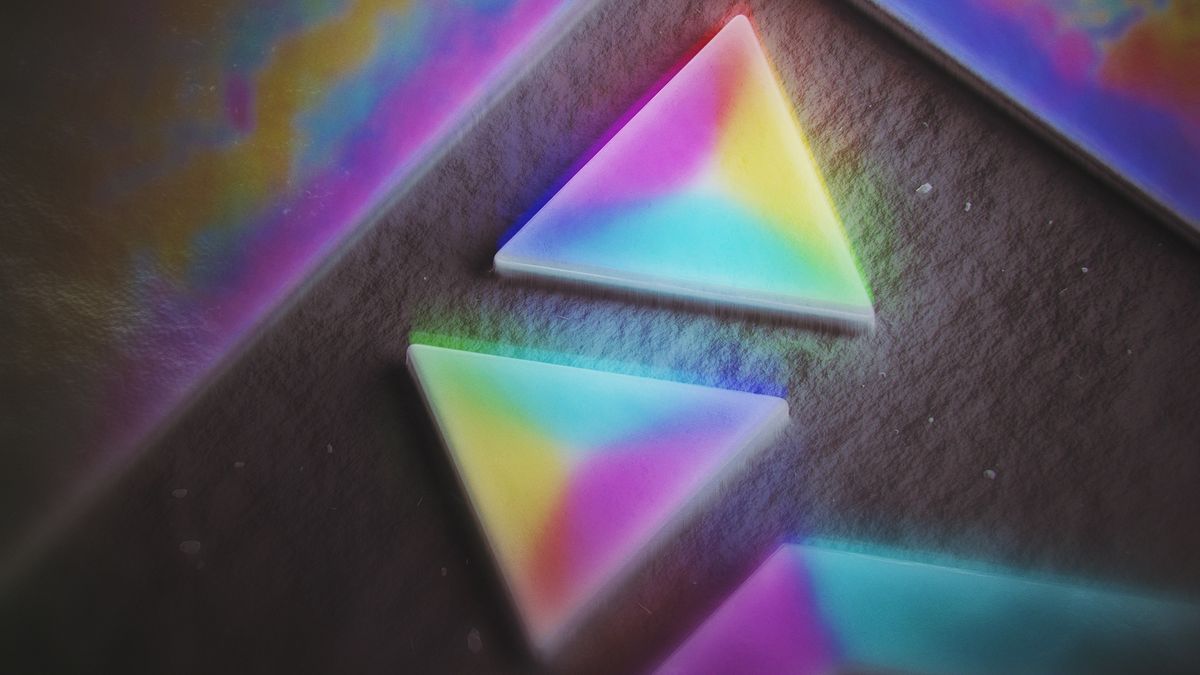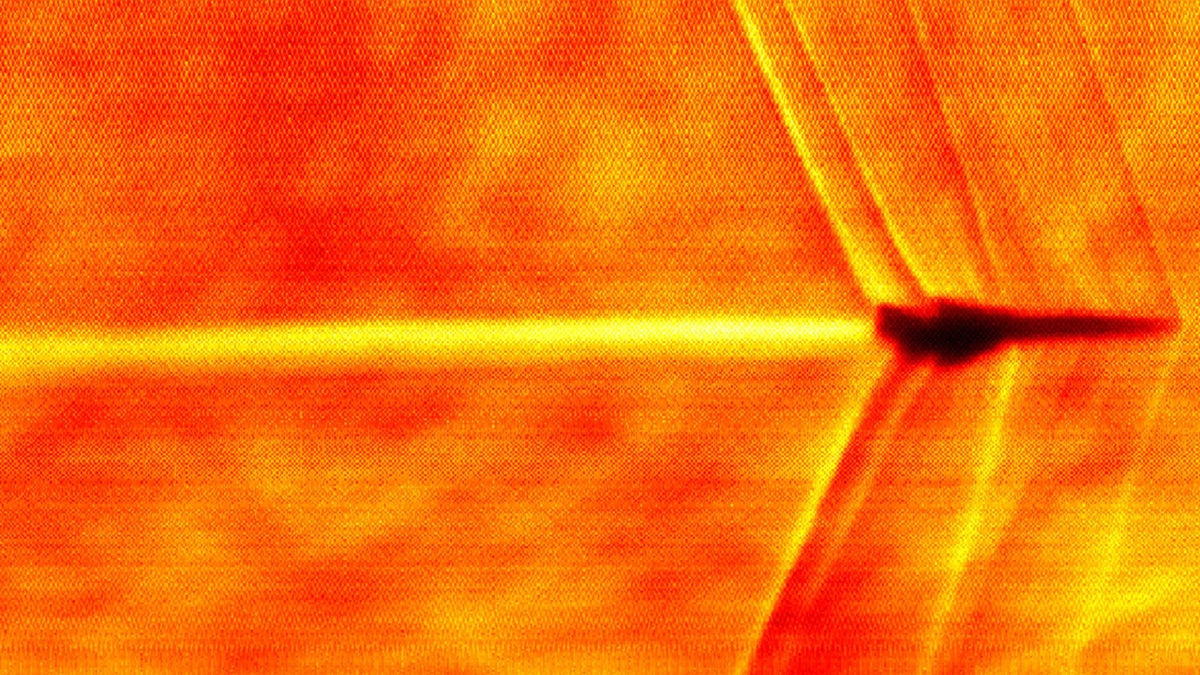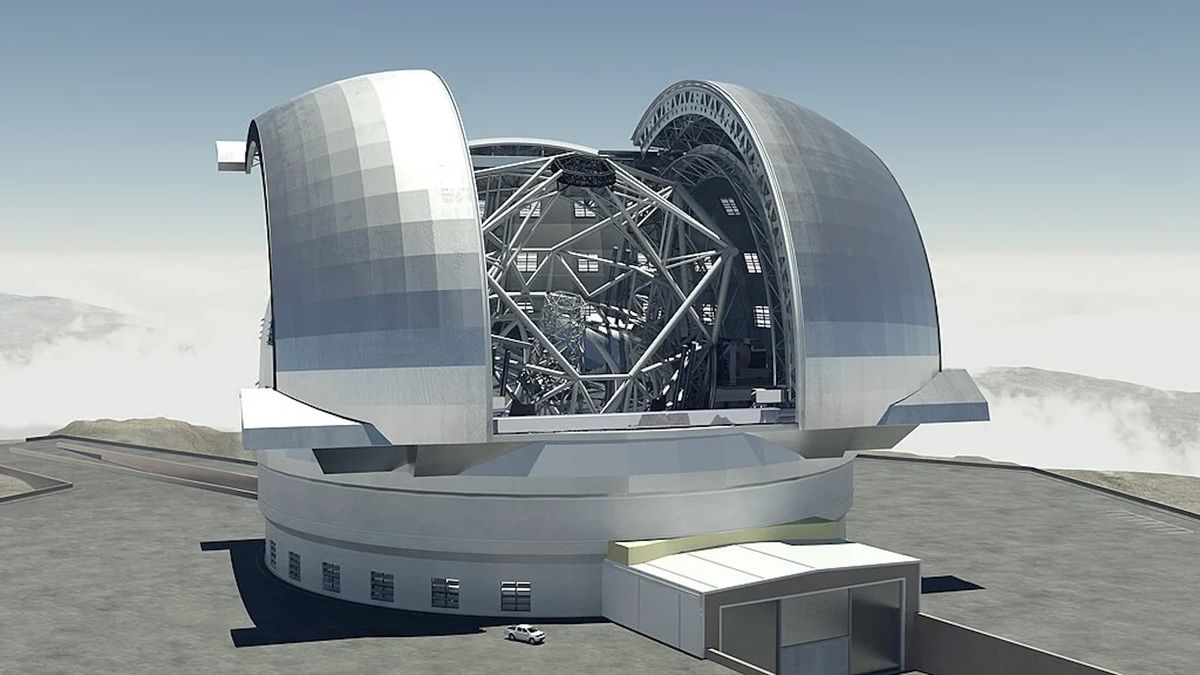上周,医学研究的黑暗章节重新开放了美国正式道歉,该道歉在过去的实验中以梅毒和淋病感染危地马拉囚犯。但是,挖掘有关1940年代后期工作的文件的医学史学家现在担心神话和现实对医学实验史的模糊。
她特别关心的是普遍认为,美国公共卫生服务研究人员在阿拉巴马州臭名昭著的Tuskegee研究中故意感染了梅毒的非裔美国人。他们没有感染男人。相反,他们没有对待他们。
领导危地马拉实验的研究人员也从事Tuskegee研究工作 - 这可能会为Tuskegee神话增加燃料。
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的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比(Susan Reverby)表示,塔斯基吉的神话仍然没有结束。她说危地马拉实际上证明了感染梅毒的人。
Reverby解释说:“我认为危地马拉表明给人们感染是多么困难。” “我曾认为这将有助于(消除)神话。”
科学家说,即便如此,这两组实验都揭示了医生在与人类受试者的道德界限上的tip脚(或运行)。许多人可能已经意识到不道德的做法。实际上,一位著名的病毒学家在他的回忆录中建议这样的实验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唯一方法。 [7个绝对邪恶的医学实验]
神话符合现实
试图在危地马拉研究期间感染梅毒的人通常意味着用皮下注射针然后将梅毒感染的液体放在该区域,或将材料注入前臂静脉。 Reverby说,如果Tuskegee幸存者肯定会召回这样的程序。他们没有。
此外,准备梅毒混合物以进行感染需要花在“宿主”兔子上的钱(其睾丸被放下用于使用的睾丸)和实验室。从1932年到1972年,塔斯基吉(Tuskegee)的记录都没有显示在这种事情上的钱。
危地马拉病例也与杜斯基吉(Tuskegee)关于另一个关键点的研究不同 - 如果研究人员感染了梅毒,研究人员实际上用青霉素治疗了危地马拉测试受试者。这是因为他们的实验着重于测试预防或治疗梅毒的不同方法。
相比之下,研究人员选择不使用青霉素在塔斯基吉(Tuskegee)治疗非裔美国人测试对象,甚至拒绝有关治疗的信息。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想看看梅毒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何在人体中进展。
塔斯基吉(Tuskegee)“是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人们使用了目的的手段,”波士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伦纳德·格兰兹(Leonard Glantz)说。 “科学的命令克服了道德。”
当法律眨眼时
公共卫生服务医师约翰·卡特勒(John C. Cutler)进行的危地马拉实验表明,研究人员愿意通过试图感染人们跨越道德界限。研究人员知道这一点:他们中间的信件表明他们担心研究泄漏的消息。
里弗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PHS当局知道这处于道德优势。” “但是,这是任何自愿同意的时期,甚至不走知情同意,尚未需要。”
在知情同意书或审查委员会批准医学实验之前,这是一个时代。尽管书籍上已经有法律,但即使有些个人医生也认为有自由将患者视为实验性测试对象。 Chester Southam病毒学家在美国为癌细胞注射了末期和健康患者。
著名的病毒学家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说:“除非法律有时会眨眨眼,否则您将没有医学的进展。”
不在树林里
公众对Tuskegee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实验的愤怒导致改革旨在维护人类测试对象的权利。但是,历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说,过去关于医学研究的问题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变异。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师和医学史学家罗伯特·阿罗诺维茨(Robert Aronowitz)说:“我们的问题发展了 - 部分是由于改革的成功,这使早期的问题很少,而且还因为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一些当前的道德问题看上去很熟悉。如今,许多医学研究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丰富的研究人员以金钱或医疗服务的诱惑与穷人接触 - 与PHS研究人员如何向危地马拉当局提供某些医疗药物或供应方式,以换取他们的合作。
阿罗诺维茨说,这种权力失衡会污染穷人同意成为人类豚鼠的想法,因为穷人面临比福利人更容易受到志愿服务的诱惑。
阿罗诺维茨告诉《生命科学》:“人们想放弃自己的身体以获取这些资源。” “如果您在试验期间提供所有这些临床服务,然后在结束时退出会发生什么?”
波士顿大学的格兰兹说,研究当今的道德问题可能比将过去的事件互相权衡更重要。
格兰兹谈到危地马拉实验时说:“我认为他们没有比塔斯基吉还差,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认为您不必互相衡量暴行。”
- 7个不再适用的可靠健康技巧
- 7绝对邪恶的医疗实验
- 十大神秘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