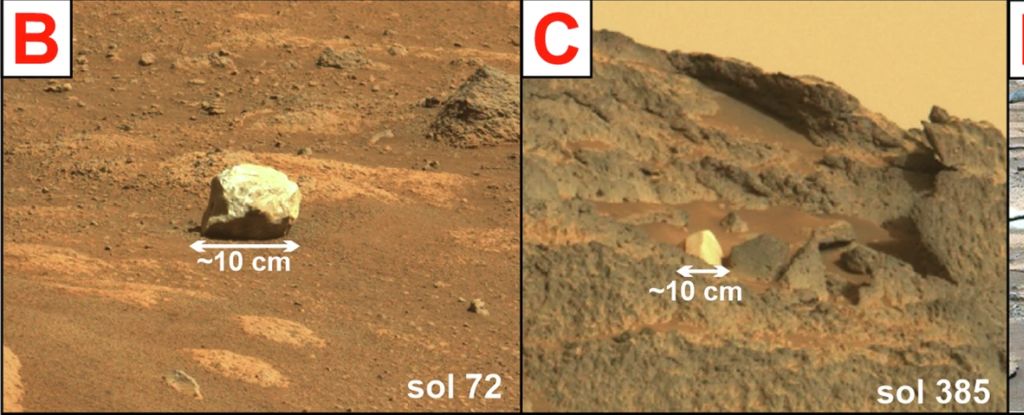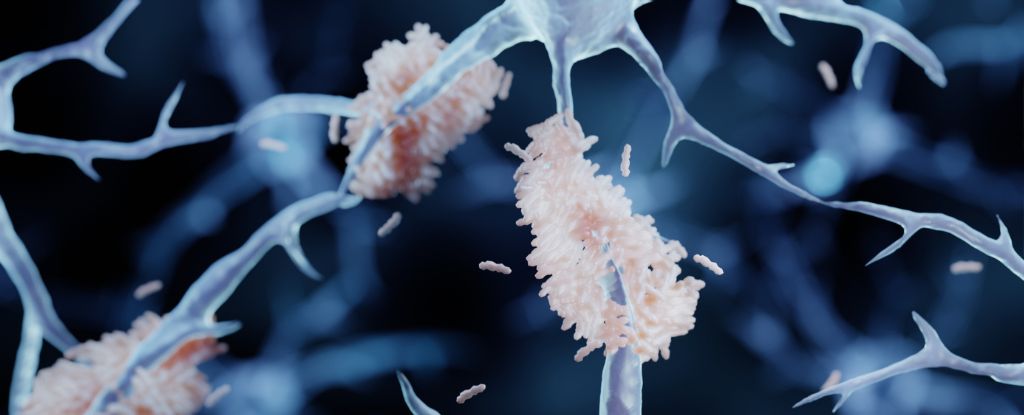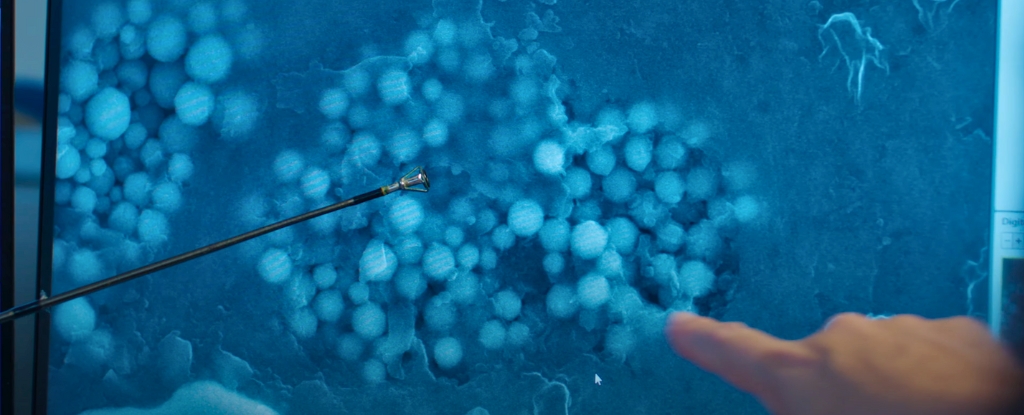想像一張你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並排的照片。你會看到相似之處,但每一代人看起來都與其前輩不同。
這是最簡單形式的進化過程:帶有修改的傳承。
經過許多代,數量驚人的修改是可能的。這就是地球上生命多樣性的形成過程。
然而,這一想法長期以來一直被誤解為一條通向“更高”或“更好”生物體的單一方向的道路。例如,魯道夫·扎林格 (Rudolph Zallinger) 1965 年著名的 Time-Life 插畫“通往之路一個聰明人”展示了人類從類人猿祖先到現代人的逐步進化。
將這一觀點擴展到人類之外,有關古代生命的早期古生物學理論支持了這一觀點定向進化,或“漸進進化””,其中每一代血統都朝著更複雜或更優化的形式發展。
但進化沒有終點線。沒有最終目標,沒有最終狀態。生物體的進化是通過自然選擇在特定的地質時刻起作用,或者簡單地通過在任何方向上沒有強選擇的漂移來起作用。
在我最近發表的一項研究中馬卡萊·史密斯當時,我們是哈佛大學的一名本科生研究實習生,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我們試圖研究生殖進化的單向模型在植物中是否始終成立。
相反,我們發現在許多類型的蕨類植物(地球上最古老的植物類群之一)中,繁殖策略的進化曾經是一條雙向街道,植物有時會“向後”進化成不太專業的形式。

進化的路徑不是線性的
選擇壓力可能會瞬間發生變化,並引導進化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
拿例如,哺乳動物。 1.5億多年來,恐龍對侏羅紀哺乳動物施加了強大的選擇壓力,這些哺乳動物必須保持體型較小並生活在地下,以避免被獵殺而滅絕。
然後,大約 6600 萬年前,希克蘇魯伯小行星消滅了大多數非鳥類恐龍。突然之間,小型哺乳動物擺脫了強大的捕食選擇壓力,最終可以生活在地面上演變成更大的形式,包括人類。
雖然多洛定律已被批評,其最初的想法已基本上從流行話語中消失,但這種觀點仍然影響著當今生物學的各個方面。
植物與進步的步伐
博物館經常將動物進化描述為向更高階段的直線進展,但它們並不是這個敘述的唯一來源。它也出現在有關植物繁殖進化的教學中。

最早的維管植物——那些具有可以在整個植物中輸送水和礦物質的組織的植物——無葉、稱為端粒的莖狀結構,頂端有稱為孢子囊的膠囊,可產生孢子。
端粒完成了植物的兩項重要工作:通過光合作用將陽光轉化為能量,並釋放孢子以產生新植物。
化石記錄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植物發展出更專門的結構,將這些生殖功能和光合作用功能分開。
穿越植物譜系,從帶有孢子的石松植物從蕨類植物到開花植物,繁殖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事實上,花經常被視為植物進化的最終目標。
在整個植物界,一旦物種進化出種子、球果和花等生殖結構,它們就不會恢復到更簡單、未分化的形式。這種模式支持生殖複雜性的逐步增加。但蕨類植物是一個重要的例外。
不斷發展,但並不總是向前發展
蕨類植物有多種繁殖策略。大多數物種將孢子發育和光合作用結合在單一葉型上——這種策略稱為單態性。其他人將這些功能分開,一種葉子類型用於光合作用,另一種葉子類型用於繁殖——這種策略稱為二態性。
如果植物中廣泛存在的特化模式是普遍存在的,那麼我們可以預期,一旦蕨類植物的譜系進化出二態性,它就無法改變方向並恢復為單態性。然而,通過使用自然歷史收藏和算法來估計蕨類植物的進化,史密斯和我發現了這種模式的例外。
在一個名為鏈蕨(Blechnaceae),我們發現了多個案例,其中植物進化出高度特化的二態性,但隨後又恢復到更普遍的單態性形式。

缺乏種子賦予蕨類植物靈活性
為什麼蕨類植物有如此靈活的繁殖策略?答案在於他們缺乏什麼:種子、花朵和水果。這將它們與當今地球上生活的超過 350,000 種種子植物區分開來。
想像一下,取出一片肥沃的蕨類植物葉子,將其收縮並緊緊地包裹成一個小顆粒。這基本上就是未受精的種子——膠囊中高度改良的二態蕨葉。
種子只是一系列生殖特徵中的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結構,每一個都以最後一個為基礎,創造出一種如此特殊的形式,以至於逆轉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由於活著的蕨類植物沒有種子,它們可以改變葉子上產生孢子的結構的位置。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並非所有植物的生殖特化都是不可逆轉的。相反,這可能取決於工廠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了多少層專業化。
在當今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了解哪些生物體或性狀被“鎖定”對於預測物種如何應對新的環境挑戰和人類造成的棲息地變化非常重要。
沿著“單向”路徑進化的生物體可能缺乏以特定方式應對新選擇壓力的靈活性,並且必須找出新的改變策略。在蕨類植物等譜系中,即使在專業化之後,物種也可能保留“向後進化”的能力。
最終,我們的研究強調了進化生物學的一個基本教訓:進化沒有“正確”的方向,沒有邁向最終目標。
進化路徑更像是錯綜複雜的網,有些分支分叉,有些分支聚合,有些甚至自身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