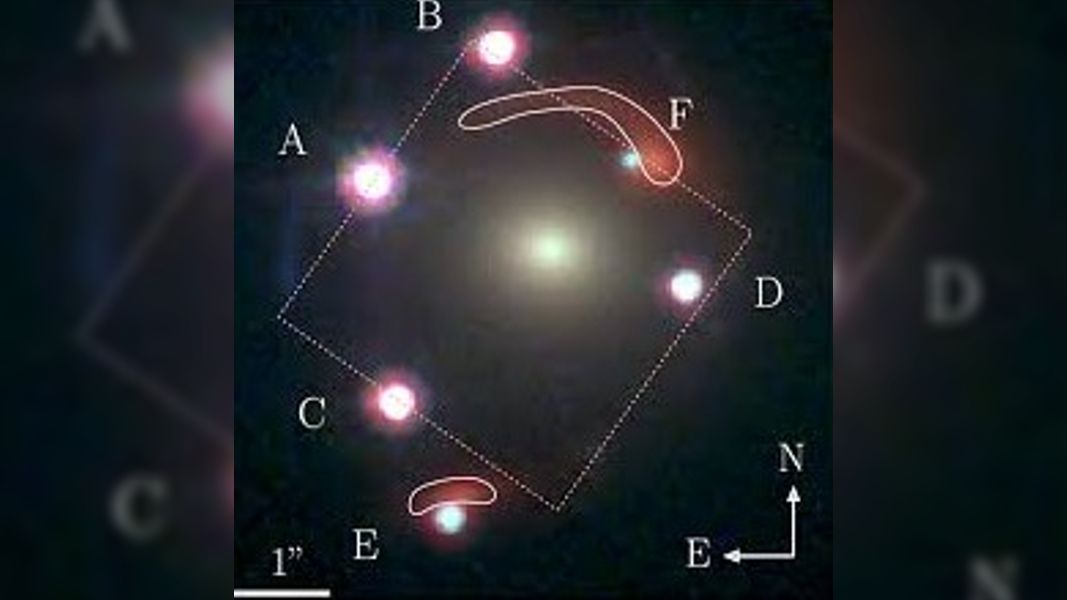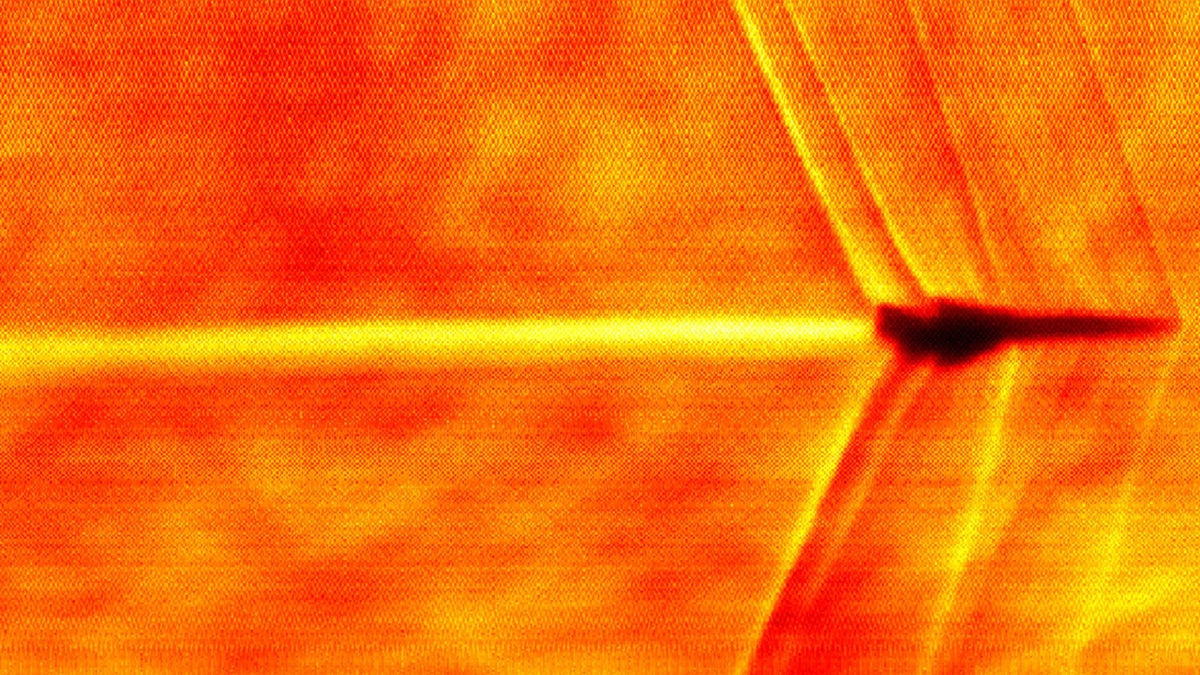对于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而言,挽救生命并延迟其终点是同一回事。使用这种逻辑,英格兰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哈里斯(Harris)的数字说,科学家有道德责任延长人类的生命范围,即使这意味着要创造永远生存的生物。
哈里斯告诉生活学。 “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致力于无限期地延长生活,这与我们致力于挽救生命的原因相同。”
但是,纽约黑斯廷斯中心的生物伦理学家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lahan)说,但是失去孩子和老年人的去世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第一个还为时过早,而后者希望在悠久的生活结束时到了。
卡拉汉说:“一个老人的死是可悲的,因为我们失去了他们,他们失去了我们,但这不是悲惨的。” “人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宇宙,因为人们死于老年。”
这只是近年来作为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的几种道德和道德论点之一目的梦不朽或至少要延长远远超出世纪之外的生命。除其他辩论外:
-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从青年源中喝酒吗?
- 如果人们寿命更长但数十年来痛苦,对自杀和安乐死的看法会改变吗?
- 在不朽的社会中,您如何为新一代腾出空间?
一个112岁的世界
这预期寿命对于美国人来说,平均是77。6年。大多数专家说,延长寿命将是一个增量过程。但是有很大的希望。
1990年芝加哥大学生物人工学家Jay Olshansky和同事计算出的一项研究,即使美国癌症死亡的风险降低到零,平均预期寿命也只会增加2.7年。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还消除了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预期寿命将再增加14年。
相比之下,重复的实验表明,啮齿动物的少量减少了40%的寿命约40%。由于尚不清楚的原因,这种“热量限制”方案还推迟了通常与衰老相关的许多退化性疾病的发作。
密歇根大学的病理学家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说,如果可以在人类中复制这些效果,那么普通人可以活到112岁,我们的最大寿命可以延长至140年。
道德上的命令
米勒说,此外,如果啮齿动物的实验是任何指南,那么未来的老年人将是适合的,平均90岁的年轻人类似于当今50岁的孩子。
由于这些原因,米勒认为,老龄化研究对改善公共卫生的影响要比试图单独治愈疾病产生更大的影响。
米勒告诉米勒告诉现场科学。
曼彻斯特生物伦理学家哈里斯说,如果延长寿命也可以延长健康,那么抗衰老研究的论点是道德上的命令。
“问,'我们应该让人们不朽吗?'并以否定的方式回答。心脏病, 癌症,失智,还有许多其他疾病,并决定我们不应该。”哈里斯认为。
但是即使人类决定绿灯抗衰老研究伦理学家说,就道德理由而言,还有其他棘手的道德问题。其中最高的是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谁可以访问?
大多数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同意,初次开发的生命延伸技术可能会非常昂贵,因此只有少数有钱人能够负担得起。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现有社会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批评家说,幸运的是,有能力负担得起疗法的人不仅要有明显更长的寿命,而且会有更多的机会积累财富或政治权力,并控制经济甚至文化机构。
但是,哈里斯指出,现代世界已经充满了类似的不公正现象。例如,在美国,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8年,但在博茨瓦纳只有34年,这是非洲艾滋病毒感染率最高的人之一。在埃塞俄比亚,艾滋病毒感染的流行程度要少得多,预期寿命为49年。
发达国家还可以使用贫穷国家无法实现的药物和救生程序,例如器官移植。然而,美国人通常不会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肾脏移植,而其他国家的人则无法获得肾脏移植。
哈里斯说,同样,只有富人才能获得寿命技术的事实并不是足够的理由禁止它。一方面,拒绝对一群人的生活治疗不会拯救另一人。其次,新技术通常开始昂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便宜,更广泛地使用。
哈里斯告诉生活学。 “所有技术都是如此。”
几个世纪的折磨
伦理学家说,另一件事是寿命会对我们一些珍贵的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例如,在美国,生命权被认为是每个人有权获得的东西,自杀和安乐死都被认为在文化和社会上都无法接受。
但是,在一个数十年来的人类生命的衡量世界中,而是几个世纪以来或几千年,可能需要重新检查这些价值观。原因之一:永生并不意味着无敌。疾病和战争仍将杀死,中风仍然会弄乱沮丧仍然会在钝化生活的乐趣。
如果有的话,某人何时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让别人为他们结束它的问题已经是一个激烈的辩论话题。如果通过告诉某人必须生活,我们将不仅谴责他们不仅要几年,而且数十年或几个世纪的折磨,答案将变得更加必要。
世代清洁
还,地球只能支持这么多人。如果每个人都寿命更长,那么几代人将不得不分开以避免人满为患。
哈里斯说,为了确保足够的世代流动,社会可能需要诉诸某种“世代化的清洁,这很难证明”。这将涉及人们共同确定一代人赖以生存的时间是合理的,然后确保个人到达任期结束后死亡。
哈里斯说,这种行动将需要我们对自杀和安乐死的态度的根本转变。人们要么不得不停止以为挽救生命很重要,要么他们不得不停止认为故意在某个时刻造成死亡有问题。
哈里斯说:“我们已经长大了对生与死的一定期望,如果这些期望改变,许多其他事情也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