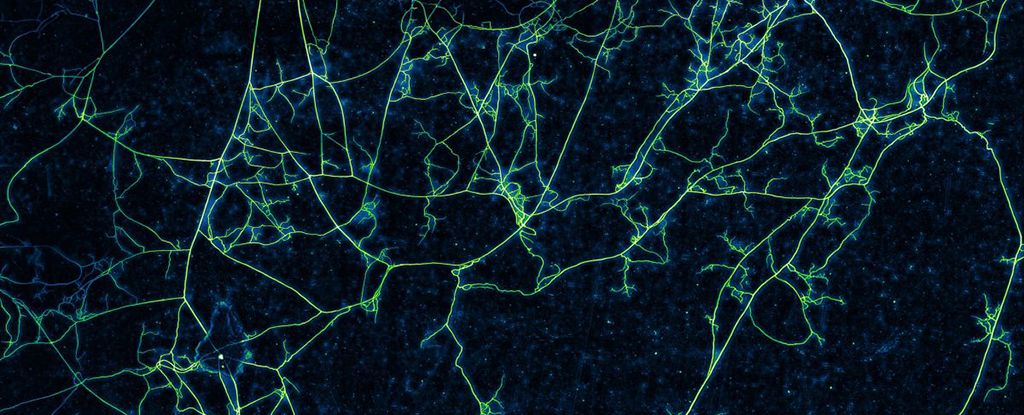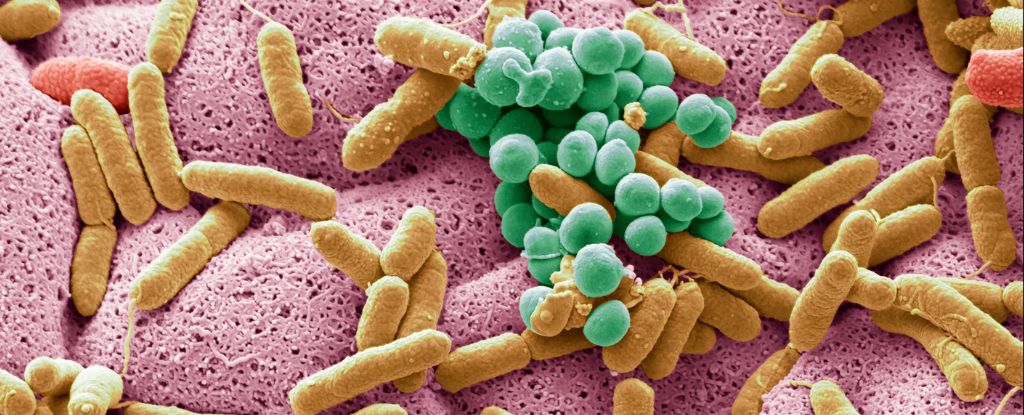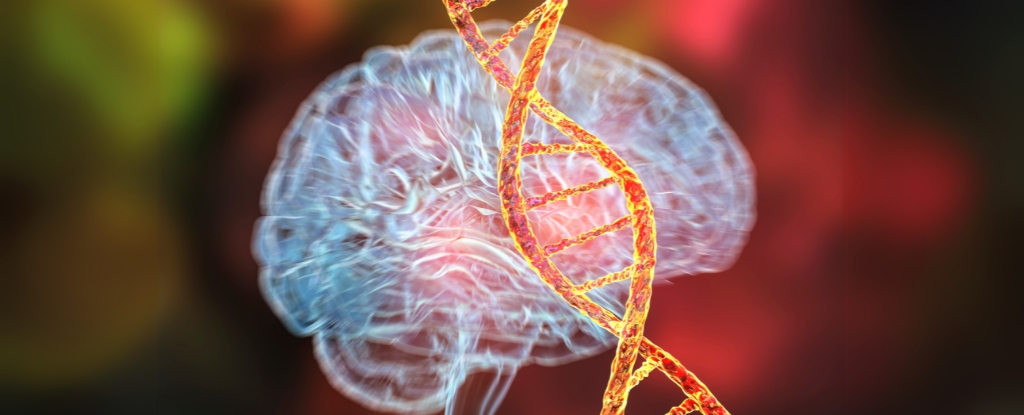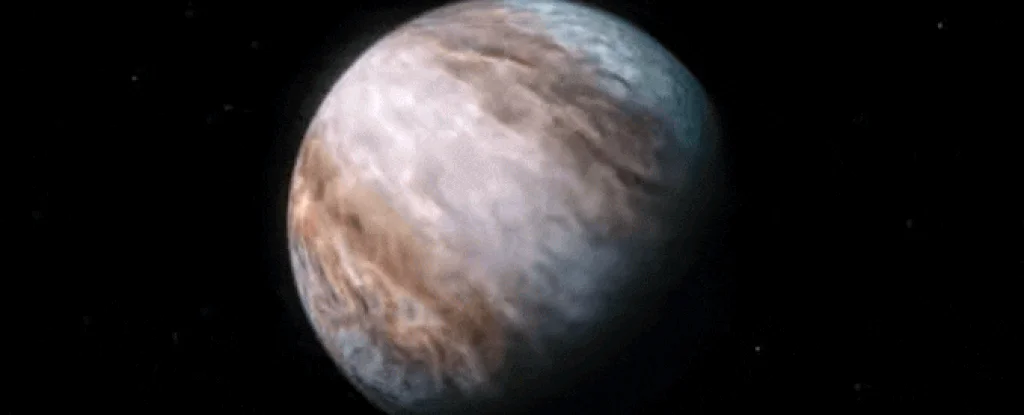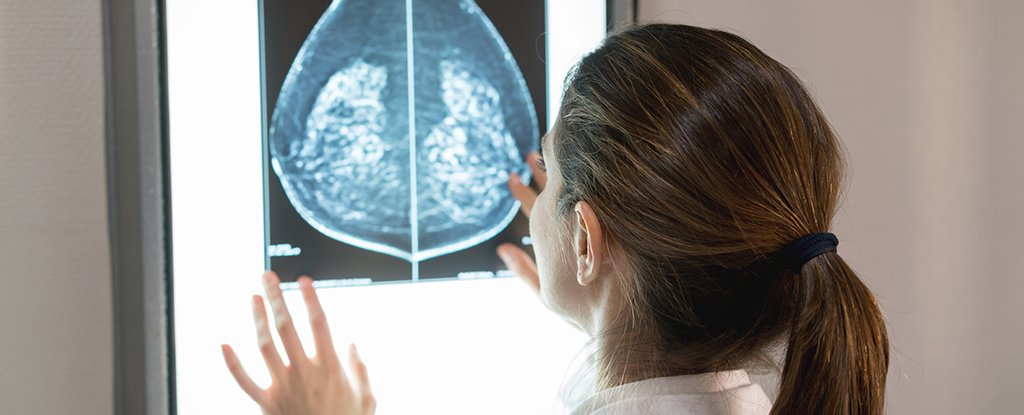地球上有許多本土問題,但我們仍然有時間擔心來自上面的壞事。最近的是小行星 2024 YR4,如果它在未來十年的最初幾年襲擊我們星球上人口稠密的地區,可能會成為“城市殺手”。
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現在估計約為 0.001%。但在這之後有一個短暫的時刻去年,當直接撞擊的估計危險超過了 1% 的舒適風險閾值時,他就發現了這一點。
如果我們想避免重蹈覆轍,就需要擔心行星防禦問題。。但還有許多其他事情可能會殺死我們,包括和戰爭。
那麼,太空中的什麼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呢?這些恐懼如何影響我們——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
從長遠來看,除非我們能夠改變方向,否則重大事件將會襲擊我們。準備工作的責任從我們開始。

然而,準備工作也存在風險。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杜德尼 (Daniel Deudney)已警告用於行星防禦的技術不僅可以引導小行星遠離地球,還可以作為軍事衝突的工具引導它們接近地球。
正如杜德尼在《黑暗天空》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他的解決方案是扭轉、規範和放棄我們的大部分人類活動都是在太空中進行的未來幾個世紀。他認為,我們在太空中做得越多,國家最終陷入災難性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
“避免文明災難和物種滅絕現在取決於辨別什麼不該做,然後確保不做,”他寫道。
他最終認為太空擴張來得太早了,我們必須扭轉這一過程,直到我們做好準備。儘管如此,他認為我們可能仍然需要某種形式的行星防禦,但它可能是有限的。
不過,推遲幾個世紀是不太可能的選擇。小行星撞擊的可能性可能太高了。還有太空擴張的政治利益此時,是不可逆轉的。

對太空的恐懼隨著太空計劃而增長。對小行星撞擊和過度軍事化的擔憂導致了對太空未知事物的更深層次的恐懼。然而,他們也傾向於擔心人類自我毀滅的一面。
這兩種恐懼由來已久。我們最早可追溯的人類故事之一,即至少可追溯到 15,000 年前的宇宙狩獵故事,將兩者結合在一起。
一個土著薩米人版本,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倖存,描述瞭如果獵人不耐煩,射出的箭沒有擊中目標並意外擊中北極星,那麼天空中的大型狩獵將會出錯。這將使夜空的天篷墜落到地球上。
再次,對人類誤導行為的恐懼和來自上述威脅的恐懼融合在一起。
我們可以從現代技術驅動的恐懼中看到這一點,例如不明飛行物學。一些UFO 的鐵桿信徒他們不僅擔心敵對的訪客,還擔心地球上科學家之間的秘密合作,或者擔心向公眾隱瞞真相的整個陰謀。
如果不相信有陰謀壓制證據,整個想法就會崩潰。但如果不相信太空中確實存在令人恐懼的東西,那麼這個陰謀就毫無意義。對空間的恐懼是這幅圖畫的必要組成部分。
中國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最近巧妙地捕捉到了這一想法。將太空比作“黑暗森林”外星文明試圖互相隱藏。
所有這一切都以某種地堡心態為先決條件,地球與太空的過度分離,或天空和地面。這就是我所提到的接地偏壓。這種偏見讓空間看起來像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外部事物,而不是我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外星病毒
這種恐懼的合理化理由不僅限於小行星、外星人、流星和失控的軍事衝突。甚至有一種理論認為來自太空。
當新冠懷疑論者尋找一個想法來解釋為什麼戴口罩毫無意義時,他們中的許多人突然想到的是一個晦澀的理論由天體物理學家 Fred Hoyle 和 Chandra Wickramsinghe 於 1979 年整理而成。
兩人最終有了一個好主意,但隨後又提出了一個壞主意。好主意是生命出現的成分可能來自太空。壞主意是它們已經形成,如病毒和細菌,而且它們仍然會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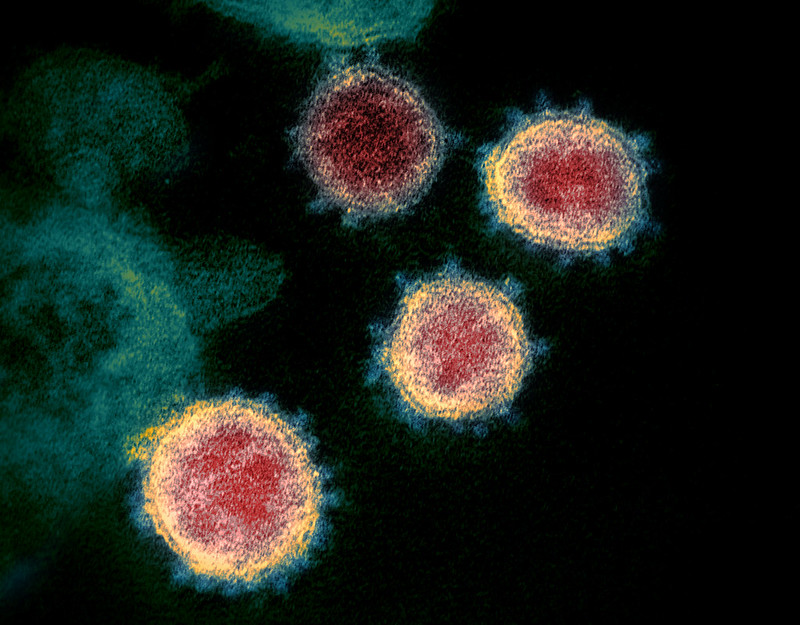
根據這一理論,過去眾所周知的流行病(例如 1918 年致命的流行病) 甚至古代的流行病)顯然是來自太空的病毒的結果,不可能是人與人之間傳播的結果——尤其是無症狀攜帶者。
新冠病毒版本涉及一顆流星在中國上空爆炸。
在採訪,威克拉姆辛格聲稱“這個火流星的一塊含有數万億的 當火流星進入平流層時,它脫離了火流星”,釋放出病毒顆粒,然後被盛行風攜帶。
這個想法說明瞭如何利用對太空的恐懼來引發對人類失敗或不法行為的焦慮。自那以後,人們對新冠病毒持懷疑態度一路走進白宮。
但對太空的恐懼也可以用來批評當權者。
在我們這個時代,它們被用來助長有關擁有私人太空議程和總統訪問權的億萬富翁、富有的太空遊客,甚至更富有的潛在殖民者的敘述。以及更遠的地方。這是一個誘人的敘述,但它認為地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不應該向外界開放。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害怕太空本身。我們當然有一種誇張的感覺,即我們在地球上與它的分離。我們確實有理由擔心一些特殊的事情。
但也存在這樣的風險:對太空的恐懼可能與對政府的懷疑結合在一起,導致我們接受陰謀論,以此將不同類型的擔憂整合為一套單一的、可管理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