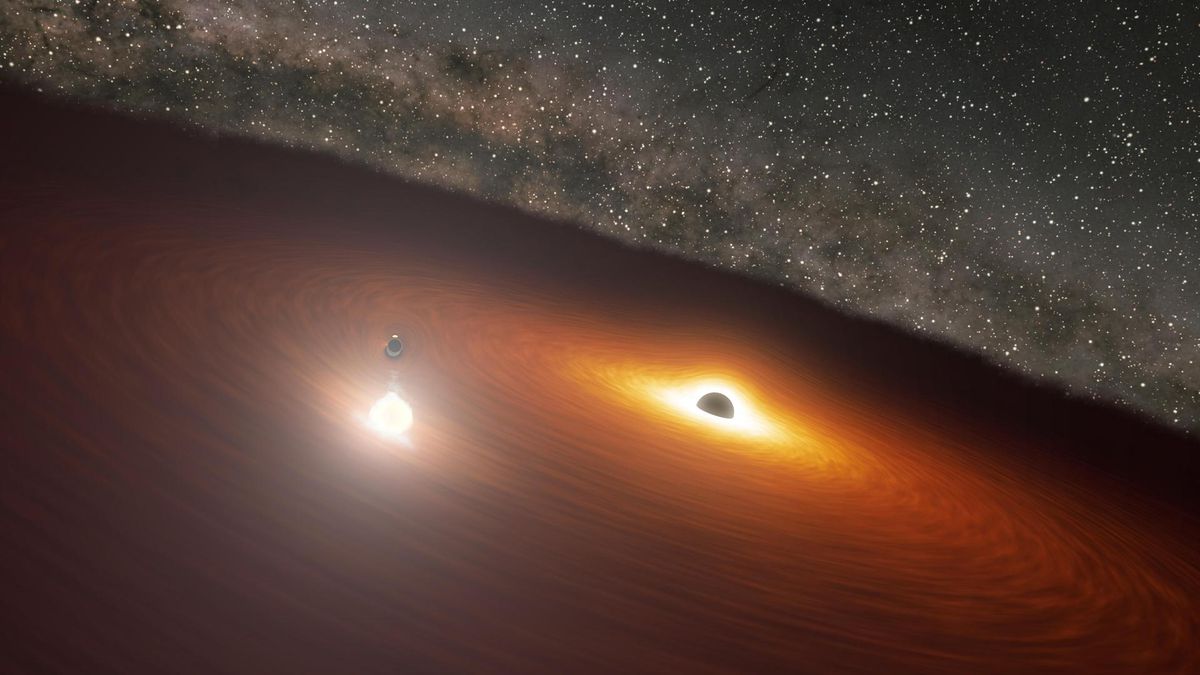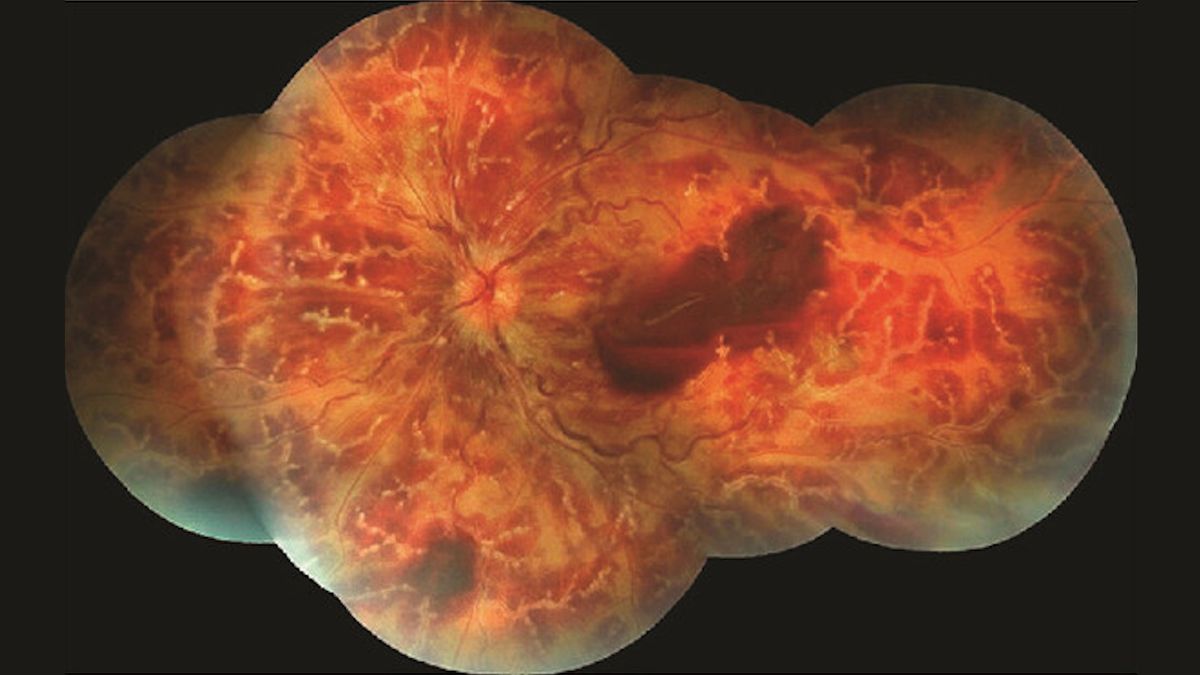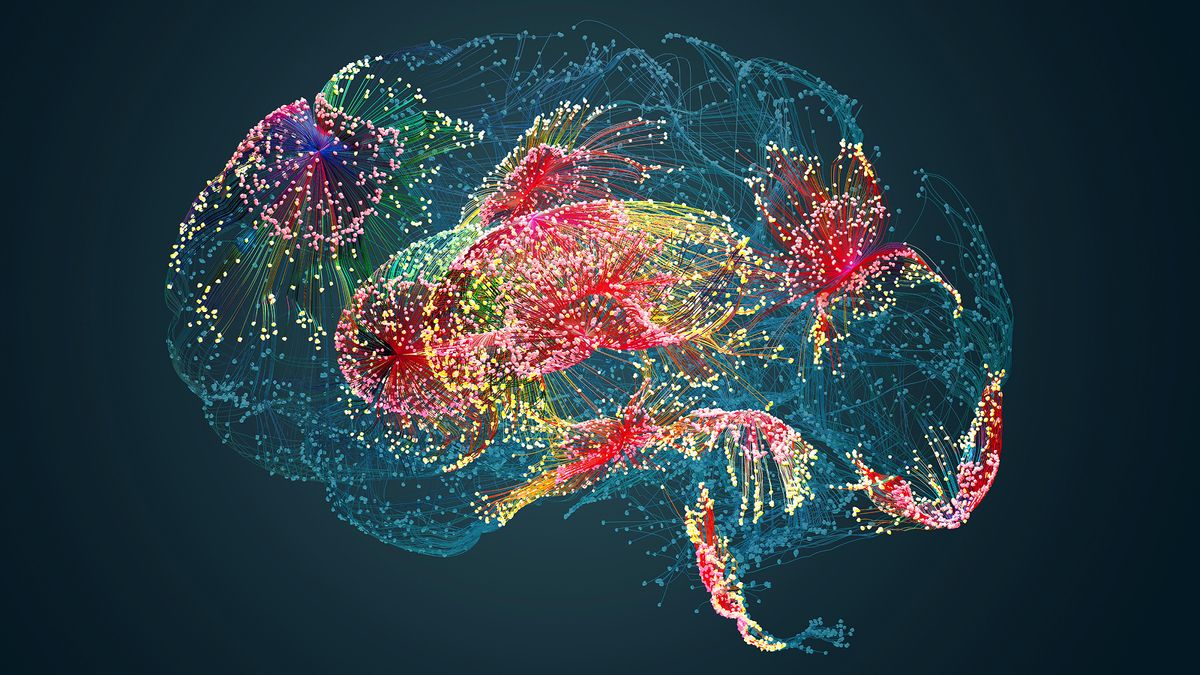在最近的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執行命令中,有人警告說:一個扭曲的敘述“關於種族”是由意識形態而不是真理驅動的。 ”它挑出了當前的展覽史密森尼美國美術館標題權力的形狀:種族和美國雕塑的故事“舉例來說。展覽展示了兩個世紀的雕塑,這些雕塑表明藝術如何產生和再現了種族態度和意識形態。
行政命令譴責展覽,因為它“促進了種族不是生物學現實的觀點,而是一種社會結構,指出'種族是人類的發明。'”
行政命令顯然反對這樣的情感:“儘管一個人的遺傳學影響了他們表型特徵,並且自我認同的種族可能受到外表的影響,種族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結構。 ”但是這些話不是來自史密森尼人;它們來自美國人類遺傳學學會。
科學家 拒絕 這個想法 那 種族 是 生物學上 真實的。關於種族是一種“生物現實”的說法,違反了現代科學知識。
我是歷史學家專門研究種族科學研究的人。行政命令將“社會構建”置於反對“生物現實”。這兩個概念的歷史都揭示了現代科學是如何降低種族是由人而不是自然發明的。
有關的:
種族存在,但這是什麼?
在20世紀初,科學家認為人類可以根據身體特徵將人類分為不同的種族。根據這個想法,科學家可以發現人群中的身體差異,如果這些差異傳給了後代,科學家已經正確地識別了種族。類型。 ”
結果“類型學“方法很混亂。一個沮喪的1871年列出了13位科學家他們確定了兩到63場比賽之間的任何地方持續存在的混亂為了接下來的六十年。種族分類幾乎與種族分類器一樣多,因為沒有兩個科學家似乎就哪種物理特徵衡量或如何衡量它們達成共識。
種族分類的一個棘手的問題是,人類身體特徵的差異很小,因此科學家努力利用它們來區分群體。開創性的非裔美國學者Web du Boish在1906年指出,“不可能在黑人和其他種族之間繪製色線……在所有物理特徵中,黑人種族本身就無法引發。”
但是科學家嘗試了。在1899年的人類學研究中威廉·里普利(William Ripley)使用頭部形狀,頭髮,色素沉著和身材的分類人員。 1926年,哈佛人類學家認真的hooton,世界上領先的種族傳統學家列出了24個解剖特徵,例如“存在或不存在後gl素結節,咽孔或結節”和“半徑和尺骨的鞠躬程度”,同時承認“這份清單”當然不是詳盡的。
所有這些混亂與科學的運作方式相反:隨著工具的改善和測量變得越來越精確,研究對象 - 種族 - 越來越混亂。

當雕塑家時馬爾維納·霍夫曼(Malvina Hoffman)的“人類種族“展覽1933年在芝加哥野外博物館開業,儘管它的定義難以捉摸,但它將種族描述為一種生物學現實。世界知名的人類學家亞瑟·基思爵士寫了展覽目錄簡介。
基思將科學視為區分種族的最可靠方法。一個人知道一個人的種族,因為“一眼就可以肯定地挑出種族特徵,而不是一群受過訓練的人類學家。”基思的觀點完全捕捉了種族必須是真實的觀點,因為他在周圍看到了一切,儘管科學永遠無法確定現實。
然而,在種族的科學研究中,事情將會改變。
轉向文化以解釋差異
到1933年,納粹主義的興起增加了種族科學研究的緊迫性。作為人類學家Sherwood Washburn1944年寫道:“如果我們要與納粹討論種族事務,我們最好正確。 ”
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兩個新的科學思想得以實現。首先,科學家開始尋求文化,而不是生物學作為人群之間差異的驅動力。其次,人口遺傳學的興起挑戰了種族的生物學現實。
1943年,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和基因Welthish寫了一個簡短的作品也標題為人類種族。他們為受歡迎的受眾寫作,他們認為人們比不同的差異要相似得多,而我們的差異歸功於文化和學習,而不是生物學。一部動畫動畫片短,後來使這些想法更廣泛。
人類兄弟會(1947) - YouTube

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韋爾菲什(Welfish)認為,儘管人們確實確實在身體上有所不同,但這些差異毫無意義,因為所有種族都可以學習並且所有種族都有能力。 “文明的進步不是一個種族或子種族的壟斷,”他們寫道。 “黑人在脫皮的歐洲人戴皮膚而不了解鐵時,就製作了鐵工具,並為衣服編織了精美的衣服。”對不同人類生活方式的文化解釋比對難以捉摸的生物種族的吸引力更強大。
轉向文化與生物學知識的深刻變化一致。

Theodosius Dobzhansky是一個20世紀的傑出生物學家。他和其他生物學家是對進化變化感興趣。因此,種族據說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改變,因此對於理解生物如何發展而毫無用處。
科學家稱之為“遺傳人群”的新工具更有價值。遺傳學家Dobzhansky認為,根據它共享是為了研究生物體的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塑造人口的發展方式。但是,如果該人群沒有闡明自然選擇,則遺傳學家必須放棄它,並根據不同的共享基因與新人群一起工作。重要的一點是,無論遺傳學家選擇的人口如何,隨著時間的流逝,它都在變化。沒有人口是一個固定穩定的實體,因為人類種族應該是。
舍伍德·沃什伯恩(Sherwood Washburn),碰巧是多班斯基的密友,將這些想法帶入人類學。他認識到遺傳學的目的不是將人們分類為固定群體。關鍵是要了解人類進化的過程。這一變化扭轉了他的老老師Hooton教授的一切。
沃什伯恩(Washburn)在1951年寫作,“沒有辦法將……人口分為一系列種族類型的劃分”,因為這樣做是毫無意義的。假設任何群體不變的群體都以理解進化變化的方式。遺傳種群不是“真實的”。這是科學家使用它作為鏡頭來了解有機變化的發明。
理解這種深刻差異的一種好方法與滾筒杯架有關。
去過遊樂園的任何人都看到了跡象表明,這些標誌精確地定義了誰足夠高到可以騎過溜冰者。但是,沒有人會說他們定義了“高個子”或“矮個子”的“真實”類別,因為另一個過山車可能有不同的高度要求。這些標誌定義了誰足夠高,只能騎這種特殊的過山車,僅此而已。它是確保人們安全的工具,而不是定義“真的”高個子的類別。
同樣,遺傳學家使用遺傳種群作為“推斷現代人類的進化史“或者因為他們對了解疾病的遺傳基礎。 ”
任何試圖用螺絲刀將指甲砸死的人很快就會意識到工具適合他們為其設計而毫無用處的任務。遺傳人群是特定生物學用途的工具,而不是將人們按種族分類為“真實”群體。
沃什伯恩認為,誰想對人進行分類,必須給予“細分整個物種的重要原因。 ”
史密森尼人的展覽顯示了種族化雕塑的方式”既是壓迫和統治的工具,也是解放和賦權的工具。
我們的談話我們從史密森尼機構獲得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