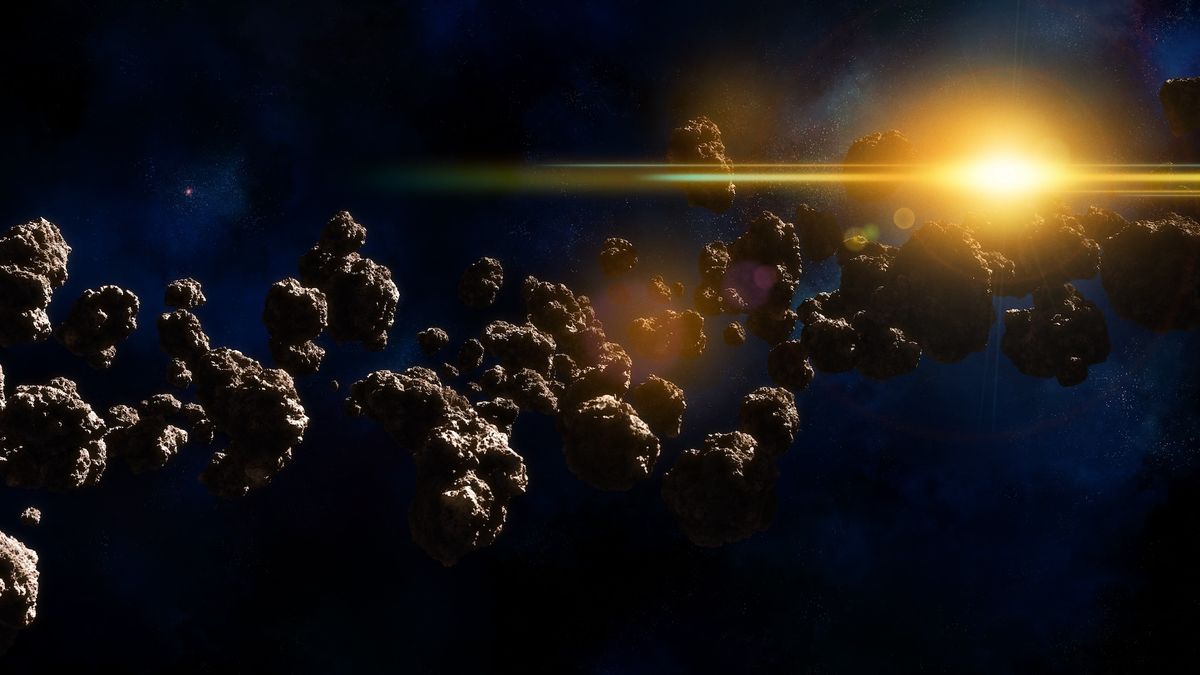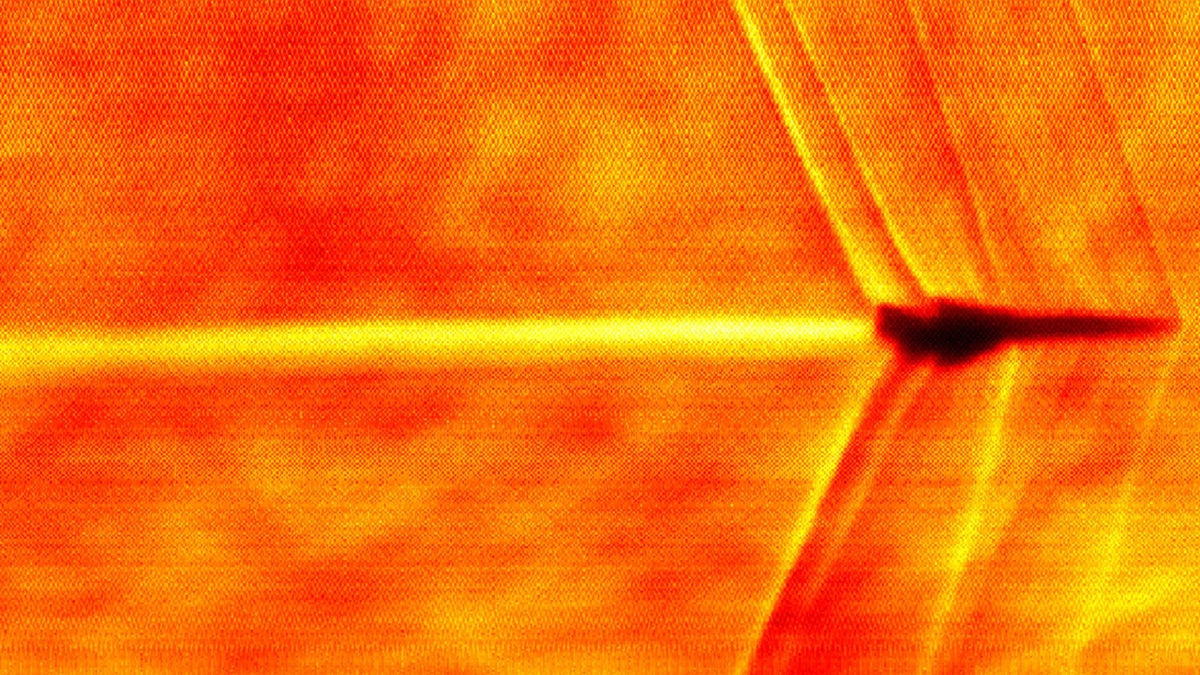2016年,科学家出版了纸以大胆的说法:长颈鹿,首先由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描述为一种物种,实际上可能是四种始终。与Linneaus不同,研究人员可以使用现代的遗传工具,该工具揭示了长颈鹿基于其DNA的差异而属于不同的簇,其中一些“大于棕熊和北极熊之间的差异”,作者当时说。
该消息使涟漪穿过长颈鹿保护界,该界突然需要保护四种而不是一种物种。但是从一开始,这种新的分类就存在分歧,甚至在今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一个监督威胁和濒危物种清单的组织)将长颈鹿列为一个物种,,,,giraffa camelopardalis,有九个亚种。
灰尘和其他类似的尘埃突出了“物种问题”,这是我们如何解析生物的根本不确定性,它继续使世界各地生物学家生气。
争论通常取决于数十年的定义。 1942年,生物学家恩斯特·梅尔(Ernst Mayr)创造了最持久的是什么:生物物种概念,如果它们不能繁殖并产生肥沃的后代,则将两个生物标记为不同的物种。此后,研究人员基于共同的祖先(系统发育概念),物理特征(形态学物种概念)或共享生态学(生态物种概念)建立了定义,其中物种在其环境中接管不同的壁ni时会产生不同。总的来说,至少有16个物种定义,有可能多达32,当今科学家之间流通。
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定义没有例外。在某些物种中,个体看起来彼此之间的不同,以及看起来相同但在遗传上截然不同的“隐秘物种”。杂交也很常见,导致了诸如Liger(狮虎杂种)和Beefalo(家庭牛与美国野牛之间的十字架)等动物。甚至有证据表明,人类曾经与其他两个古老的人类繁殖,这些人类通常被视为单独的物种,尼安德特人和Denisovan,暗示他们毕竟可能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有关的:“尼安德特人比人类更重要”:您的健康如何取决于我们长期祖先的DNA

“我们设定的某些规则行不通,有时会变得很混乱,”乔丹·凯西(Jordan Casey)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海洋科学学院的海洋分子生态学家告诉现场科学。 “人类天生就想在事物上订购,甚至我也必须做出很多决定,即我是否只是看到个人之间的多样性还是试图将事物不必要地弯曲成不同的物种。”
但是,固定物种的定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练习 - 世界上许多保护政策都是围绕物种构成的,作为事实上的保护单位。最终,它也提出了更多的存在问题。毕竟,如果有四种长颈鹿,那么如果一个人灭绝了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现在群体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应该如何在生命之树中命名和订购物种以及在出现争议时如何处理的指导原则。实际上,生物学家说,即使它不是完美的,提出一份商定规则的工作清单也至关重要。
“这很混乱”
物种的概念是古老的。例如,在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写了《动物史》,其中他描述了单个动物以及群体之间的差异。
但是直到1700年代中期,分类法的概念(对生物的正式分类)才真正脱颖而出,并被Linnaeus变成了正式的纪律。随着全球科学家开始命名新物种,分类学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随着领域及相关物种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
科学家已正式描述大约200万物种和其他物种不断根据新证据而被添加或重新分类。即使对于大型,看似良好的动物,调整也相当普遍,而长颈鹿,非洲大象和逆戟鲸等标志性动物也接受了审查。
问题在于,科学家无法就可以将生物与哺乳动物,鸟类,鱼类,植物和细菌分类为多样化和不同的生物体达成共识。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练习是否有用,并指出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科学家一直在继续进行,并且随着世界的生物以惊人的速度丢失,仍然需要这样做。

“我们甚至在上面有一个名字之前就失去了东西,因此我们绝对需要继续推动以促进我们的保护目标,”特里·戈斯林纳(Terry Gosliner)这是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一名进化生物学家和分类学家,他在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发现了数千种物种,他告诉Live Science。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搁置一个物种是什么的问题,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前进。”
当今的科学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物种问题。有些人试图将现有定义与现代方法调和,例如通过将Mayr的生物物种概念重塑为遗传物种概念,这仍然表明无法再现,但将机制专门与遗传不相容联系起来。
科学中有许多概念缺乏统一的含义,而在不确定性的空间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管理。
Yuichi Amitani,Aizu大学
其他人继续发展新的想法。Jeannette Whitton,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代码开发了回顾性生殖社区概念。这个概念没有采用严格的定义,而是鼓励科学家拥抱不确定性,并承认物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 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生物是由过去的力量塑造的。
以这种整体观点结合了几个现有定义的整体观点,这意味着即使没有明确的定义,科学家仍然可以做出预测或解释自然现象。惠顿告诉《现场科学》,她和一个同事花了七年的时间来解决最终语言,部分原因是要调和自己矛盾的想法是多么挑战。
还有其他人认为将物种问题放在一边,并指出问题本身可能会分散注意力。Yuichi Amitani,日本Aizu大学生物学高级副教授,在2022年指出科学家担心缺乏共识会导致沟通崩溃,并使比较研究并没有通过。
他告诉《现场科学》,他补充说:“科学中有许多概念缺乏统一的含义,我们仍然可以很好地管理。

面对“分类法”
在许多方面,保护是这些情绪沸腾的地方,科学文献中发表了激烈的辩论。 2017年,莱斯利·克里斯蒂迪斯(Leslie Christidis),澳大利亚南十字大学的分类学家,在纸生物学对新描述的物种的持续爆炸(他称为“分类无政府状态”)使保护主义者在指导资源或集会支持方面具有挑战性。
克里斯蒂丝告诉现场科学,这个想法确实是有争议的,促使有180多名科学家共同签名公众谴责。但是克里斯蒂迪斯坚持认为,他从不意味着分类法没有保护地位。他说,相反,他在提倡统一框架用于命名新物种和管理争议。
确实,随着科学家开发了更复杂的工具,可以将分类法与基因组学,标记研究,建模甚至机器学习相结合,很明显,最佳解决方案可能不是一个适合所有既适合的定义。
探测新物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多的物种。什么时候托马斯附近,耶鲁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调查了鱼类的进化史,他经常发现分开的物种,包括几种流行的运动鱼,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让科学带领我们去哪里,这并不一定是更多物种,”近近说。
现在,工作组正在尝试建立新的准则。这生活目录例如,正在制定在每个生活王国中命名的规则,而其他群体则刻画了较小的难题。这海洋物种的世界登记册正在追踪海洋物种,而猫专家小组正在重新评估世界重罪的分类学。
克里斯蒂迪斯(Christidis)领先努力合并三个现有的鸟类物种清单,并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报告。在有争议的2016年论文之后鸟类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说,基于新的定义,该领域显然是由于估算所需的。幸运的是,该组织的努力表明:“一旦提出了所有证据,通常有可能达成共识(即使不是普遍的同意)”。从那里开始,更容易就哪种物种最需要保护。
克里斯蒂迪斯说:“作为科学家,我们都想保护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认为从共同的理由开始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