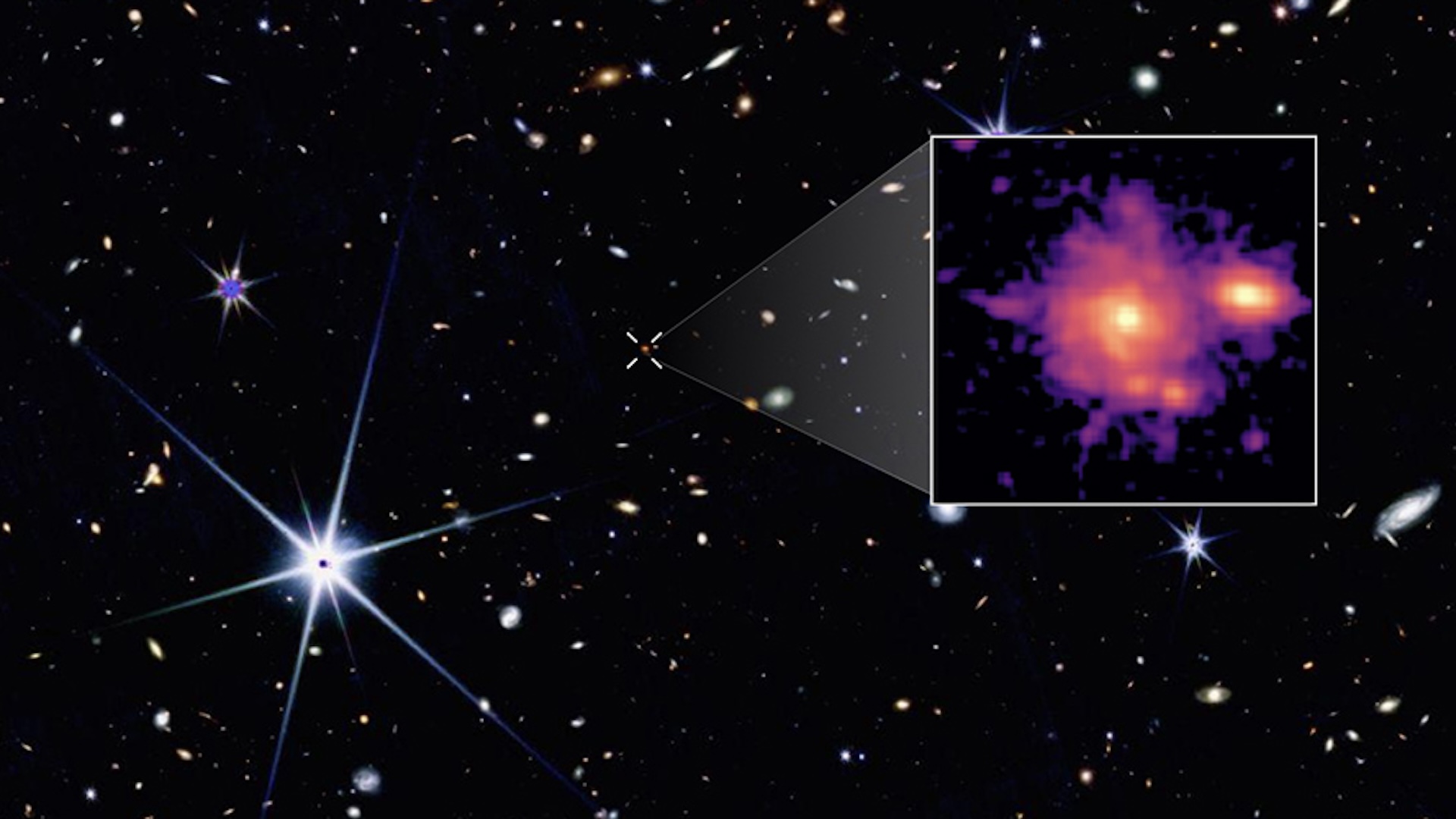上週,醫學研究的黑暗章節重新開放了美國正式道歉,該道歉在過去的實驗中以梅毒和淋病感染危地馬拉囚犯。但是,挖掘有關1940年代後期工作的文件的醫學史學家現在擔心神話和現實對醫學實驗史的模糊。
她特別關心的是普遍認為,美國公共衛生服務研究人員在阿拉巴馬州臭名昭著的Tuskegee研究中故意感染了梅毒的非裔美國人。他們沒有感染男人。相反,他們沒有對待他們。
領導危地馬拉實驗的研究人員也從事Tuskegee研究工作 - 這可能會為Tuskegee神話增加燃料。
馬薩諸塞州韋爾斯利學院的醫學史學家蘇珊·里維比(Susan Reverby)表示,塔斯基吉的神話仍然沒有結束。她說危地馬拉實際上證明了感染梅毒的人。
Reverby解釋說:“我認為危地馬拉表明給人們感染是多麼困難。” “我曾認為這將有助於(消除)神話。”
科學家說,即便如此,這兩組實驗都揭示了醫生在與人類受試者的道德界限上的tip腳(或運行)。許多人可能已經意識到不道德的做法。實際上,一位著名的病毒學家在他的回憶錄中建議這樣的實驗是取得任何進展的唯一方法。 [7個絕對邪惡的醫學實驗]
神話符合現實
試圖在危地馬拉研究期間感染梅毒的人通常意味著用皮下注射針然後將梅毒感染的液體放在該區域,或將材料注入前臂靜脈。 Reverby說,如果Tuskegee倖存者肯定會召回這樣的程序。他們沒有。
此外,準備梅毒混合物以進行感染需要花在“宿主”兔子上的錢(其睾丸被放下用於使用的睾丸)和實驗室。從1932年到1972年,塔斯基吉(Tuskegee)的記錄都沒有顯示在這種事情上的錢。
危地馬拉病例也與杜斯基吉(Tuskegee)關於另一個關鍵點的研究不同 - 如果研究人員感染了梅毒,研究人員實際上用青黴素治療了危地馬拉測試受試者。這是因為他們的實驗著重於測試預防或治療梅毒的不同方法。
相比之下,研究人員選擇不使用青黴素在塔斯基吉(Tuskegee)治療非裔美國人測試對象,甚至拒絕有關治療的信息。他們的理由是他們想看看梅毒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何在人體中進展。
塔斯基吉(Tuskegee)“是更大的遺產的一部分,人們使用了目的的手段,”波士頓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倫納德·格蘭茲(Leonard Glantz)說。 “科學的命令克服了道德。”
當法律眨眼時
公共衛生服務醫師約翰·卡特勒(John C. Cutler)進行的危地馬拉實驗表明,研究人員願意通過試圖感染人們跨越道德界限。研究人員知道這一點:他們中間的信件表明他們擔心研究洩漏的消息。
里弗比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PHS當局知道這處於道德優勢。” “但是,這是任何自願同意的時期,甚至不走知情同意,尚未需要。 ”
在知情同意書或審查委員會批准醫學實驗之前,這是一個時代。儘管書籍上已經有法律,但即使有些個人醫生也認為有自由將患者視為實驗性測試對象。 Chester Southam病毒學家在美國為癌細胞注射了末期和健康患者。
著名的病毒學家托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說:“除非法律有時會眨眨眼,否則您將沒有醫學的進展。”
不在樹林裡
公眾對Tuskegee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實驗的憤怒導致改革旨在維護人類測試對象的權利。但是,歷史學家和生物倫理學家說,過去關於醫學研究的問題並沒有消失,而只是變異。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醫師和醫學史學家羅伯特·阿羅諾維茨(Robert Aronowitz)說:“我們的問題發展了 - 部分是由於改革的成功,這使早期的問題很少,而且還因為我們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一些當前的道德問題看上去很熟悉。如今,許多醫學研究都在發展中國家進行,資金豐富的研究人員以金錢或醫療服務的誘惑與窮人接觸 - 與PHS研究人員如何向危地馬拉當局提供某些醫療藥物或供應方式,以換取他們的合作。
阿羅諾維茨說,這種權力失衡會污染窮人同意成為人類豚鼠的想法,因為窮人面臨比福利人更容易受到志願服務的誘惑。
阿羅諾維茨告訴《生命科學》:“人們想放棄自己的身體以獲取這些資源。” “如果您在試驗期間提供所有這些臨床服務,然後在結束時退出會發生什麼?”
波士頓大學的格蘭茲說,研究當今的道德問題可能比將過去的事件互相權衡更重要。
格蘭茲談到危地馬拉實驗時說:“我認為他們沒有比塔斯基吉還差,但是話又說回來,我認為您不必互相衡量暴行。”
- 7個不再適用的可靠健康技巧
- 7絕對邪惡的醫療實驗
- 十大神秘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