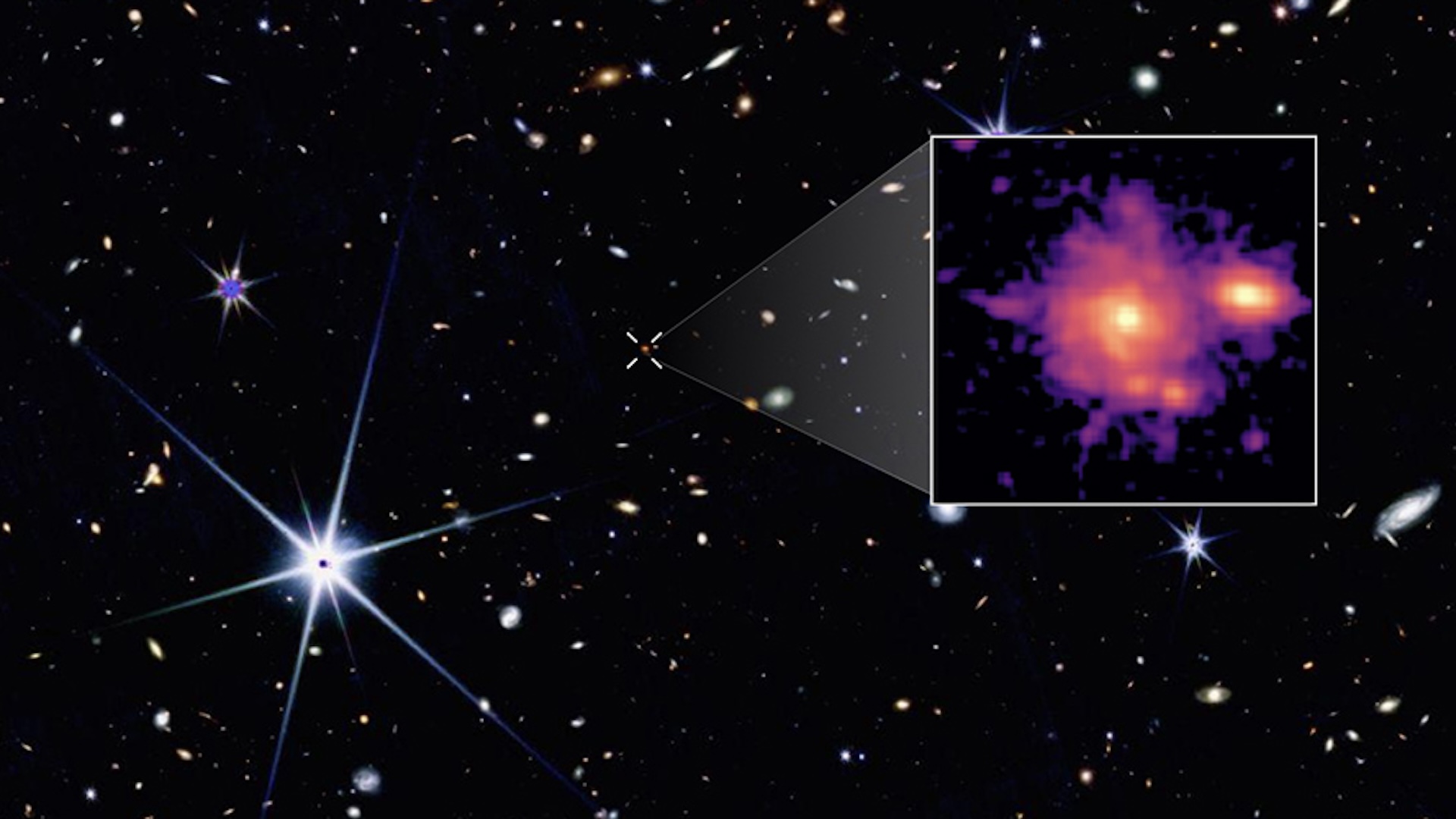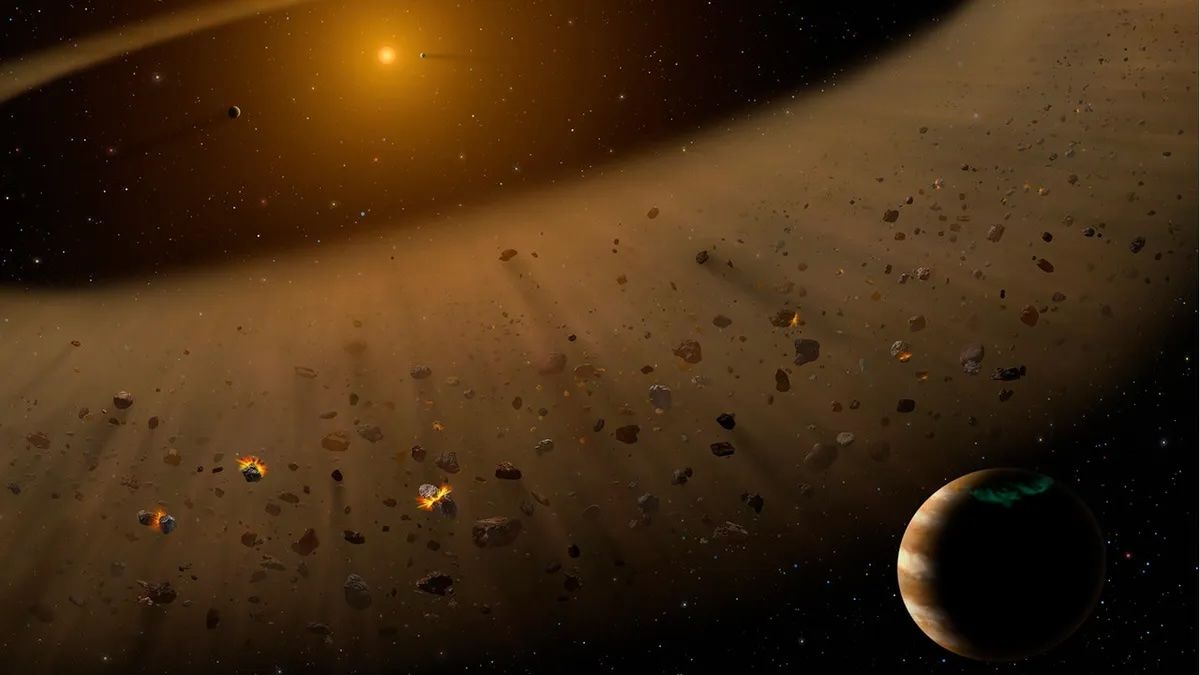在33個被困的智利礦工到達地表之後,在救援膠囊中一一一個一一逐一地,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他們經歷了兩個多月的隔離和黑暗將結束。但這不會像他們知道的那樣重新生活的盡頭。
這些人面臨著潛在的身體問題,從真菌感染到到達表面後的眼睛。有可能心理問題例如創傷後應激障礙。可能會發現,重新融入他們的生活和人際關係是壓力很大,因為親人可能沒有他們的生活適應生活。然後是媒體要處理的眾多,以及不可避免的書和電影提議。
但這並不一定是痛苦的。其他從類似經驗中恢復過來的人報告說,對生活有一種新的陶醉感。
本·舍伍德(Ben Sherwood)是“倖存者俱樂部:可以挽救您生命的秘密和科學”(Grand Central Publishing,2009年)的作者,他的研究使他得出了一個簡單的結論:“單一的共同點是,人們比他們意識到的要強得多,而且更具彈性。”
途中
8月5日,智利北部的一個金色和銅礦的屋頂倒塌了,捕獲了33個礦工,他們在地面以下約2200英尺(670米)的地方庇護所。 8月22日,由救援人員鑽出的第一個鑽孔到達了礦工,並用表面開了一條生命線。 [信息圖:智利礦山崩潰這是給出的
儘管據報導,智利衛生官員準備治療維生素D缺乏症(由於缺乏陽光),但由於缺乏延長的光線和真菌性疾病而導致的肺部疾病部分塌陷,而眼睛造成的眼睛損害是由於延長的地下造成的,但前往地表的旅行卻有其自身的醫療問題。
上升時間的估計有所不同,但邁克爾·鄧肯(Michael Duncan)NASA副首席醫療官說,他認為現在大約是15-20分鐘,最初為2.2 mph(1米/秒)的速度。
鄧肯今天(10月12日)在電話採訪中說:“如果他們要在那個受到關鍵的籠子裡引起人們的關注,那麼在旅行過程中可能會有暈倒或昏倒的風險。”
預計礦工將在宇航員稱為“流體裝載方案”的情況下將鹽水放下,以防止暈倒。鄧肯還與智利同事進行了討論,這些服裝可能會使中央血流流動,儘管沒有任何詞會被使用。
一旦礦工到達地面,就會明亮,沙漠的陽光與。儘管他們的眼睛應該像從黑暗到光線時一樣調整,但他們會戴太陽鏡以減輕過渡。鄧肯說,此外,太陽鏡應有助於防止其角膜損壞。
鄧肯說:“與我們的智利同事討論的關注點是,由於暴露於紫外線而引起的角膜刺激,類似於雪盲的風險。”
總體而言,礦工似乎健康狀況良好,儘管將向患有健康狀況的人(包括患有肺部疾病的人,另一名患有糖尿病的人)額外關注。
“即使他們沒有被困在礦山中,當他們在礦山工作時,他們也會暴露於非常塵土的條件,“鄧肯說。“他們已經接觸到這些條件的68天不斷暴露。這可能會引起一些問題。 ”
他說,將對礦工進行任何呼吸道感染的評估,並將受到監測,以確保他們不會對肺部有任何惡化。即使有與塵土飛揚的環境相關的健康風險,礦工仍被允許在受到限制的同時吸煙。
鄧肯說:“稱重風險效益比,覺得允許礦工在短期內吸煙比醫療風險更好地應對壓力。”
智利醫生採取了預防健康計劃,例如遣散肺炎的疫苗鄧肯說。過去照顧一個生病的家庭成員的礦工管理醫療服務。
長途跋涉
當他們的身體修補時,他們的思想也可能需要舉重。礦工有風險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西北大學的臨床精神病醫生唐·凱瑟爾(Don Catherall)表示,這是由創傷事件以及焦慮或抑鬱症帶來的嚴重焦慮症,他專門從事創傷及其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凱瑟爾告訴《生命科學》:“他們應該尋找的主要事情是他們是否覺得自己仍然落在洞穴內,重新體驗了它,好像他們從來沒有出來,即使他們有。”
他說,效果可能會延遲,因此等待六個月才能看他們的狀況是合理的。
加利福尼亞大學的舊金山精神科醫生尼克·卡納斯(Nick Kanas)研究了宇航員的心理學以及在壓力和孤立條件下工作的其他人的心理學。
卡納斯說:“我們已經研究過的宇航員和其他孤立的人……重要的是要給他們私人時間,以便在與家人和朋友分開幾個月後,他們可以重新融合。”
他說,對海軍潛艇的男人家庭的研究發現,他們的妻子和家庭適應了他們的缺席,但是當這些人回家並想重新確定自己的角色時,一些家庭經歷了不和諧,抑鬱和其他困難。
第二個壓力源
據估計,礦工上方的營地包含來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名記者。預計媒體瘋狂會向礦工致意,並談論書籍和電影交易。媒體報導,礦工在準備中接受了智利前記者的媒體培訓,並表示他們想達成法律協議以分享任何交易的收益。
根據卡納斯的說法,強烈的關注可能會沉迷於返回家人的壓力。
他說:“這些人將突然成為一個不習慣的角色。”
舍伍德說,礦工及其家人似乎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
舍伍德說,一個家庭向一名礦工發送了一張帶有貓王的照片的紙條,告訴他很快他會比貓王更出名。
末端的燈
通過採取措施,例如建立內部情感支持小組,與親人開放交流並分為三個轉變,讓睡眠,工作和放鬆,礦工和救援人員在管理狀況的壓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研究了紐約市巴布拉羅大學的壓力和傷害生活事件的社會成分。
Poulin說,礦工與表面之間的交流尤其會產生“大加”。 “他們幾乎確定隧道盡頭有一個燈。他們知道這會很好。
一旦第一個鑽孔到達礦工,救援人員估計可能需要多達四個月取回它們。
鑑於研究表明,經歷創傷性或壓力性事件的人具有彈性,Poulin對礦工很樂觀。
他說:“我的猜測是伴隨著他們所面臨的挑戰的普遍積極情況,他們將全部或一般而言。”
欣快
拘留的某些影響可能是微妙的。
作為生物圈2任務的一部分,塔伯·麥卡勒姆(Taber MacCallum)在一個封閉的生態系統中進行了兩年的歷史,在他的重新進入期間注意到了兩件奇怪的事情。
“我沒有將鑰匙放回口袋的習慣,並確保車門被鎖定了。我們在整天活著的日常生活中積累了數百個小習慣,可以幫助我們獲得,我們沒有任何這些。”
他還發現他欣賞生活。
他說:“我真的很喜歡我第一次做的一切。第一個草莓,第一個漢堡包,第一個比薩餅,第一批啤酒。” “我有點像一個成年的孩子一樣重新體驗世界。”
舍伍德說,那些在創傷事件中倖存的人可能會有類似的感覺。
他說:“生活本身,當你接近死亡時,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陶醉的事情。”
根據舍伍德(Sherwood)的說法,烏拉圭橄欖球球員之一南多·帕拉多(Nando Parrado)在1972年的飛機失事後,在安第斯山脈(Andes)被困住了兩個半月。
生活科學的斯蒂芬妮·帕帕斯(Stephanie Pappas)和珍娜·布萊納(Jeanna Bryner)向本文貢獻了報導。
- 十大神秘疾病
- 關於男性身體的5個神話
- 7個驚人的超人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