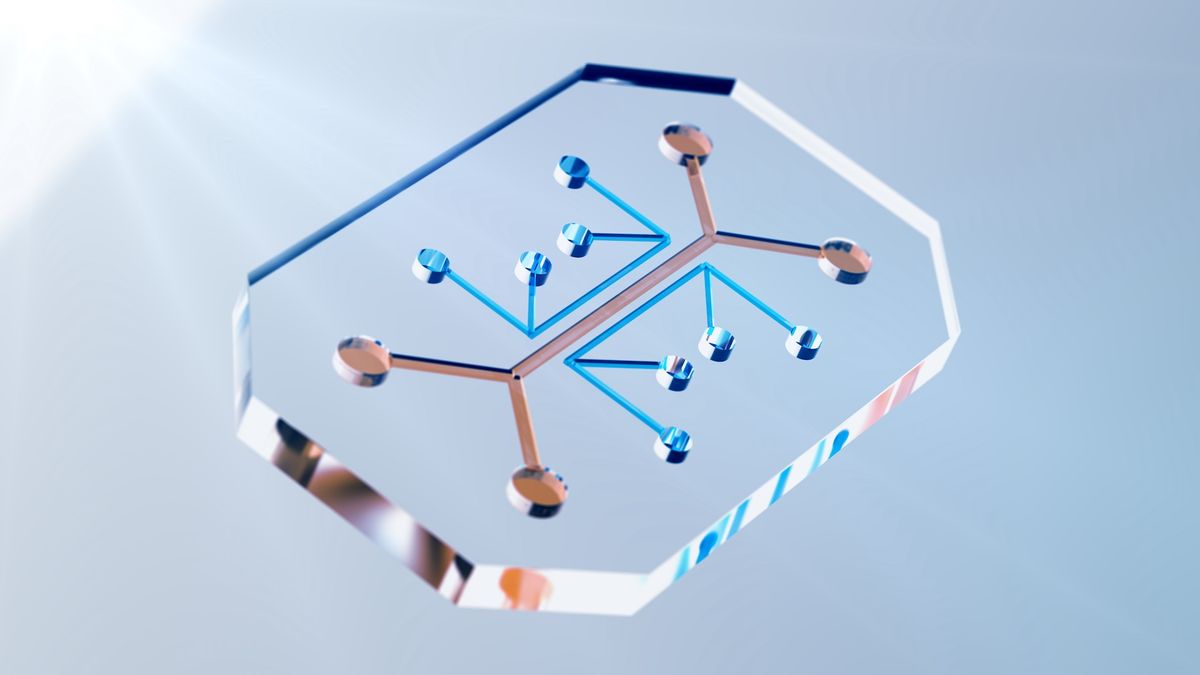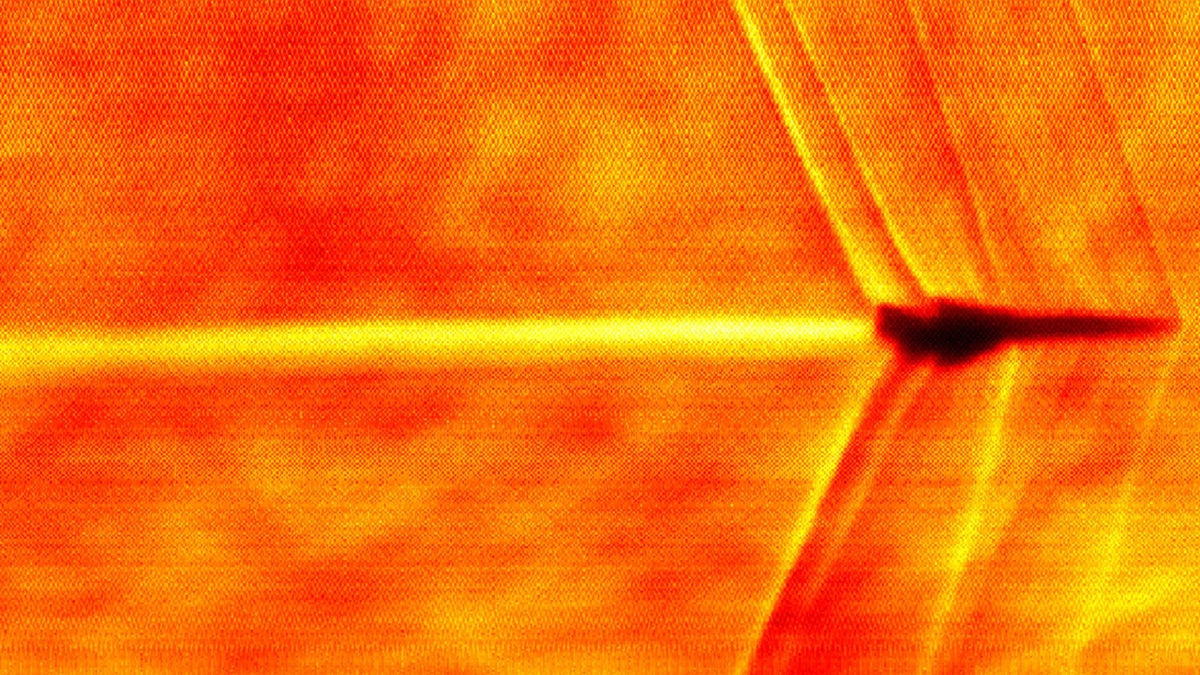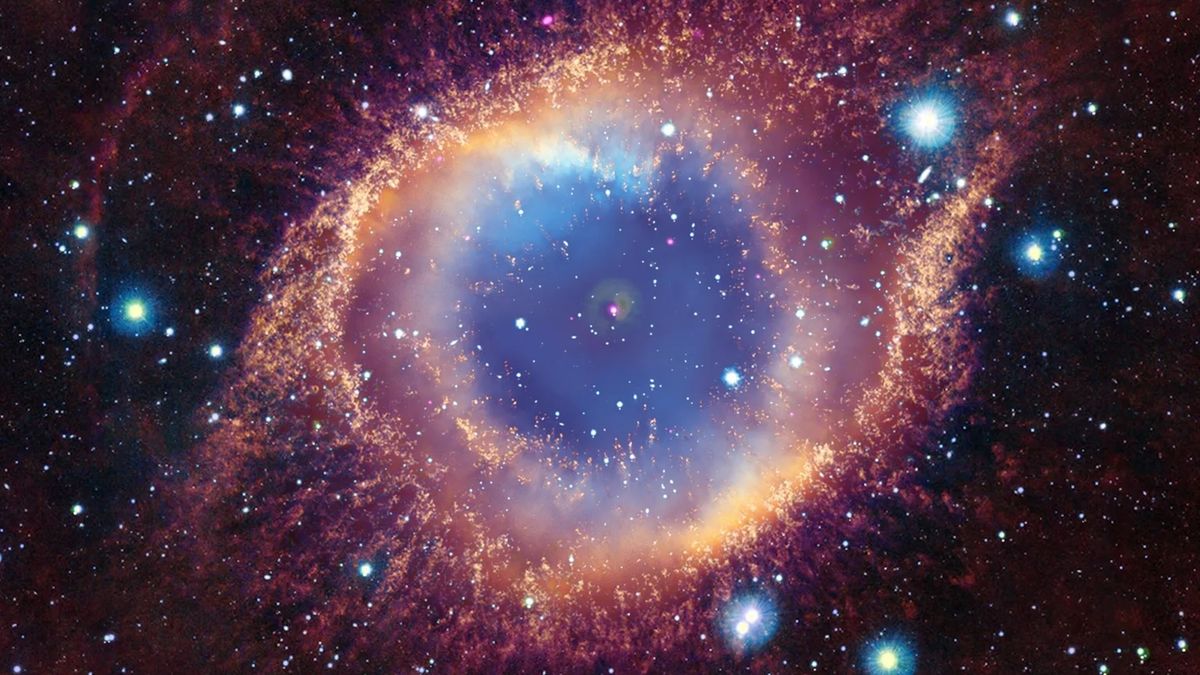本·西蒙斯(Ben Cimons)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长大,现在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的一家康复屋里,他已经干净整洁了四个月。这个专栏是从一个改编的文章那首先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卫生科于2014年2月11日。 Cimons为Live Science贡献了这篇文章 专家声音:专家和见解。
最近,我收到了母亲的电子邮件,并链接到令人痛苦的故事一个16岁的北弗吉尼亚女孩,她用海洛因过度服药并去世,他的同伴抛弃了她的尸体。我妈妈写道,她发现了这个故事:“恐怖,因为那很容易成为你。我每天都感谢上帝不是,而且你是安全和健康的。”
她是对的。可能是我,几乎是。唯一的区别是,在我从意外的海洛因过量的情况下昏倒后,我和我在一起的人打了911,然后放弃了我。
今天,我今年23岁,住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的一家康复屋里,慢慢地重新获得了我的生活。但这并不容易。
海洛因很诱人。撞到您的那一刻,所有的担忧消失了。您对一切都满意。你感到温暖。你忍不住微笑。你感到自由。我第一次尝试它时,我发现只要记得我一直经历的悲伤和孤立感。但是,一旦海洛因抓住了你,它就永远不会放手。
海洛因最近在新闻中广为人知,最近是由于死亡,显然是过量,演员菲利普·西摩·霍夫曼(Philip Seymour Hoffman)。海洛因无处不在。很容易找到,包括在我直到最近居住的郊区,而且比处方药。
您不必是富裕或著名的或犯罪分子就会上瘾。我在一个不错的贝塞斯达(Bethesda),社区中长大,有一个从不喝酒,抽烟或使用任何非法物质的单身母亲。但是我和我一起出去的附近的孩子们做到了。我想适应中学和高中,并停止感到孤独。这就是我开始通往过量的道路。
9月16日,我妈妈睡着了,遇见了我的朋友,我开车去华盛顿州东南部寻找海洛因。我们俩都在车上射击。我记得开始开车,但是随着我后来得知,我昏昏欲睡,跌倒在喇叭上,阻止了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通。我停止了呼吸,嘴唇变成紫色。我的朋友已经处于试用期,打了911电话,然后逃离了。
当我醒来时,仍然在车里,我被警察和护理人员包围。显然,他们给了我Narcan,这种药物几乎立即逆转了海洛因的影响。他们带我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急诊室,一位医生告诉我我有多幸运:“您躺在30秒钟的时间里,如果我们在五分钟内没有到达您,您将死亡或脑死亡。”
我开始哭泣。我还很年轻。我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
当我开始在中学时尝试毒品时,它主要是杂草,而我在高中时的使用量增加了。但是我愿意尝试任何事情 - 除了针。到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几乎一直都很高。我放学前,上学期间通过上课和午餐吸烟。当妈妈出去跑步或睡着时,我在家里抽烟,当我出去walk狗时。我被停学两次,并因拥有和发行大麻而被捕,这是我的记录撤消的指控 - 在我最终意识到我需要帮助之前。我向妈妈承认,妈妈立即安排了治疗。最终,我结束了一个住宅计划45天。 [研究表明,止痛药滥用可能导致海洛因]
离开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进行了几次短暂的复发,但最终使用我在康复中学到的工具保持了三年半的待遇,例如认识到我想要与其他人一起使用并与他人一起恢复的触发器,并将自己奉献给我自己,并将自己奉献给我12步,进行精神饮酒和毒品恢复。那时,我还是蒙哥马利学院的一名学生,仍然住在家里,希望从事刑事司法事业,可能是一名警察。自6岁起,我就一直是一名竞争激烈的游泳者,尽管我有吸毒,但仍在高中成功游泳。现在,在大学期间,我还曾担任游泳教练,赚了很多钱。
然而,大约18个月前,一种认真的关系结束了,我感到脆弱。逐渐地,我不再与我的毒品恢复赞助商和支持网络的成员交谈,并开始放开康复中获得的所有技能。
我想念我的老邻里朋友,我已经避开了三年以上的时间来保持清洁,并希望他们回来。我以为我可以处理。然后,我开始过夜狂欢 - 毒品丰富的电子音乐音乐会。慢慢地滑入我的旧习惯非常容易。我开始使用俱乐部毒品Molly,一种摇头丸的形式,然后再次除草。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罪恶感杀死了我,但是这些毒品使这些感觉匆忙消失了。
我第一次尝试海洛因的那天晚上,在2012年11月,我在该地区的一个朋友家中,另外七个人正在射击,抽烟并打nort。他们给了我一些东西,我决定打nor。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正在使用一种我说我永远不会碰触的药物。我感到放松,开始点头。很快,我会定期打nor。
几个月后,有人建议我注入它。他说:“这比打屁股好得多。”我以为我永远不会把针头放在手臂上。我讨厌针。我几乎无法处理流感疫苗。但是我决定尝试一下,我简直不敢相信它的感觉有多美妙。
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一根针和一袋海洛因。
不久,它不再是如此出色。这是必要的;我需要它。一旦开始注入海洛因,就无法回去。您的生活变成了无底洞的坑。您不再意识到自己,也无法爬出它。你撒谎,作弊,偷和典当。
我会在两天内赚钱,在我和一个朋友之间赚到价值800美元的涂料。没有它,我无法走24小时。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开始遭受经典的迹象提取:流鼻涕,出汗,肌肉酸痛,震颤和屋顶焦虑。丝毫的事情会让我离开。我开始在妈妈面前进行情绪崩溃,后者以为我仍然很干净。我欺骗了所有人 - 她,我的老板和我的治疗师。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活变得多么危险。我做的唯一聪明的事情是使用干净的针 - 我担心轨道标记和艾滋病毒。
去年六月,我回到了我第一次尝试海洛因的房子里。我整天都在射击。已经很晚了,我正要再次射击。我的一个朋友警告我,我要使用太多。我耸了耸肩,注射了自己。然后一切变黑了。这次,我自己醒了。每个人都盯着我。有人说我已经过量了,跌倒了,几乎没有呼吸。他们几乎无法感觉到我的脉搏。当我昏倒时,显然他们试图把我带上汽车带我去医院,但是我醒了,尖叫着让我放下我。
那六月的事件是我第一次意外服用过量,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警告。但是我忽略了它。我的生活是一场残骸。
即使在9月16日过量服药之后,当我接近死亡时,我也无法停止。在最初的48小时内,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赞赏。但是一旦撤离开始,我又一次射击了。
两个星期后,我度过了一个晚上,赚了价值400美元的涂料,并意识到我已经有了。我很累。我再也不能活下来了。我打电话给我的长期治疗师,告诉她我需要见她。我向她介绍了我一直在注射海洛因的消息,她敦促我回去康复 - 并告诉我妈妈。最初,我抵制,然后同意。

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在康复设施中找到了一个位置,马里兰州哈弗雷·德·格雷斯(Havre de Grace)的阿什利神父阿什利(Ashley),我准备出发。我整天哭了。那天晚上,我绝望地试图爬出窗户,去警察更多。我妈妈抓住了我。取而代之的是,我的一个朋友从表面上说再见了 - 那天晚上,我又变得高高了。第二天,在上车去阿什利之前的几分钟,我再次射击。
那是10月3日,我上次使用海洛因。
接下来的28天在阿什利(Ashley)度过,在那里我重新学习了我需要知道的知识,以避免再次复发。我再次致力于保持干净。我知道我不能很快回到贝塞斯达。压力和旧的影响仍然存在,恐怕我会再次屈服。
我想搬到一个距蒙哥马利县足够远的新城市,让我重新开始。他们说,阿什利(Ashley)的辅导员建议:不要带他回家,甚至打包。直接去威尔明顿。
我住在一所还有其他15位康复瘾君子的房子里。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跟随12步,彼此背上。我在这里学会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且我可以没有毒品生活。我现在知道我可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正在慢慢与母亲修复纽带。威尔明顿是一个大型康复小镇,所以我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我很高兴我在这里。我很高兴我想再次生活。我有梦想。我想要一个家庭。我想体验生活。现在,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本文改编自郊区海洛因瘾君子描述了他的刷子死亡和对更好生活的希望“在《华盛顿邮报》中。表达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出版商的观点。本文的此版本最初发表在现场科学。